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第十二屆林榮三文學獎.短篇小說獎二獎】 林新惠/虛掩 -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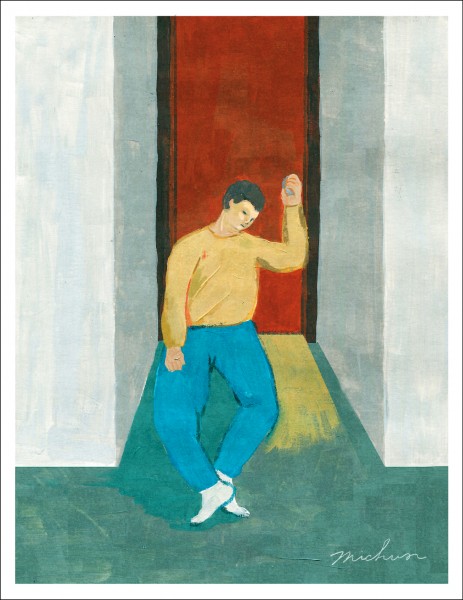 圖◎michun
圖◎michun
作者簡介:
 林新惠
林新惠
林新惠,1990年生,東吳音樂系畢,現就讀政大台文所。曾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雙溪文學獎。誤打誤撞從普通班跨入音樂系,又誤打誤撞從音樂探入文學。曲折的路上是文字撐持著每一個搖晃的時刻。
得獎感言:
頒獎當天,我正好碰上和〈虛掩〉中的女兒一樣的痛。每回都痛得那麼侵奪意識,那麼滲蝕骨肉,熬過之後,我總會恍惚地想,活回來了。頒獎這天,又活回來了,且在寫作上領受許多祝福鼓勵,真好,真感激。一個月的折騰剛結束,一輩子的文字路才正開始,我願如此。
★★★
◎林新惠 圖◎michun
七七之後翌日,妻回來了。
那天,他從前晚七七結束後的昏睡醒來,已是第五十日的正午。髮際和脖子悶蒸一層黏膩的汗,電風扇徐徐調頭過來,麻癢癢的。起身摸至冷氣遙控器,抬眼才發現定時關機的冷氣早已停止,室溫顯示三十度。
就這麼坐在電風扇的低吟中,許久,許久。倒不是昏沉,也沒在追憶,他只是非常困惑:今天該做什麼?
已經無事可做了。四十九日以來,他接獲許多表單,死亡證明書、殯葬費用請款單、骨灰暫存所需的聯絡明細、放棄急救同意書、家祭公祭流程。他寫過很多次,自己的名字、妻的名字、他們的關係、電話、住址、身分證字號。作七法事決定在家裡進行,法師說,這裡才是亡者安適之所。殯葬業者牽線聯繫到的作法團體,以「法師」為LINE的名稱,妻後第三日加他為好友,從此他時常和這「法師」LINE。他猜LINE的那一頭應該是幾個人共同管理這個「法師」帳號,因每一次對話,回覆他的遣詞總有些不同。他遵循LINE來的指示,在第五日清空客廳,下午便有人扛著鐵架、布幔和佛像,組裝靈堂,妻在三尊佛像及紅燭黃燈之中對他微笑。之後就是每一次七日,按照LINE的法師指示,準備貢金,跪奉披衫跨入客廳的法師。每週的這一天女兒不會加班,總是在法會開始前半小時就回家,布置花果、飯食、揀除殘香與斷燭。女兒在第三十天請假,那天告別式,業者說日子合適,他禁不住淺淺一笑,沒有回答,那天是他們的結婚紀念日。告別式後尚有五七、六七,及至七七,法師一面念禱,一手執妻的照片,一手取靈堂上一燭火就之,燃點邊緣後墜入鐵桶,併以咒符、連日積累的殘香斷燭。繼骨灰後他又眼見妻幻化一垛煙灰。靈堂拆落,恭送法師及佛像,四十九日結束。五十日開始,滿室僅存尚未消散的煙味,以及他一人,坐在床沿,恍然無所事。
卻是此時響起鈴聲,使他醒轉。戴上老花眼鏡,按開手機,法師向您傳送圖片。再點開,圖的底色緞紫,背景坐落巨大蓮花,其上覆蓋疏密不一金色標楷粗體字:「往事已矣,來者可追。生者當放下不捨亡者的執念,多為稱誦法號,迴向亡者。另也應整理分送亡者之物,為其多結善緣,布施有所需者。肉身雖朽,因緣仍存,常提正念,南無阿彌陀佛。」他選取「Thank You」貼圖,傳送,法師已讀,不回。
揉眼起身,他決定依法師所言,開始整理妻的衣物。踱出房間,行經女兒臥房,瞥一眼,女兒早上班去了。走廊轉彎是浴室,而後客廳,他望向玄關彼端,棲著女兒的室內拖鞋。再右轉就該是妻的房間,他不假思索正要直接走進去,卻險險撞上關起的房門。
壓下門把,才驚覺,是鎖著的。又反覆試了幾次。是鎖著的。
睡得太長的混沌瞬間抽起一絲精明的思緒,晶晶瑩瑩纏繞:房門只能從裡頭手動上鎖或從外頭以鑰匙上鎖、鑰匙因根本用不著連放在哪都不知道、這扇門是房間唯一的對外通道、女兒不在。
思緒糾結眼裡,融為液體。那一刻,他毫無疑心。妻回來了。
他敲敲門,輕喚妻的名字。然後等待。門會打開,或者不會,他其實不太確定比較希望哪一個發生。如果妻來應門,那該說些什麼呢。仔細想想,這還是第一次和妻分別這麼久。結婚之後,他們就是鑲嵌在這屋子裡了,唯一獨自離開的時候就剩他偶爾出差,那也不過三週以內的事。總之就是相識而後結婚,日日夜夜看著對方臉形身形髮型逐漸離當年愈來愈遠。卻也相去不遠。人還是那人,無論來應門的是前些日子臉上身上橫滿急救管子的妻,或是初識時一雙眼轉得精明剔透,貓一般玲瓏輕巧的妻,他都認得。
再敲一次門,妻的名字又從嘴裡滾落,他聽得出有些顫抖,兩個字落在木質地板,碎入沉默。
時間凝結,他摒住呼吸,身體暫停在敲門的姿勢。
什麼也沒發生。
日光在玄關那頭,淹進窗子,車聲人聲潮起潮落,仍然運轉的現實世界排浪而來,他鬆懈呼出僵持已久的氣息,依著門滑坐地板。
妻回來了。但妻沒有開門。法師說的整理遺物這下做不成了。可是妻回來了,那還算遺物?要不傳LINE問問法師?還是等女兒下班,告訴她吧?
地板和門板的溫度涼涼地滲進他的身體,恍恍惚惚,才剛睡醒的他,又漸漸盹著了。
再度醒來,是女兒打電話回家裡,說今天要加班,要他自己先吃,晚上也早點睡,別等門了。
終究,妻回來的那天,他沒能告訴女兒。而關於女兒,他則有好多想和妻聊聊。
妻回來的隔天,他起床後巡過一圈家裡,女兒不在,妻的房門仍如昨天鎖著。沒辦法動妻的衣物,只得將這一個多月來他和女兒堆積的衣服丟進洗衣機。半小時後一件件抖開,他才發現這裡頭完全沒有胸罩。後陽台薰熱的風拂過晾衣桿上每個衣架,黑色襯衫、深灰色T恤、又是黑色襯衫、深藍色襯衫、白色襯衫、西裝褲、西裝褲、西裝褲……若不細查其間尺寸和裁剪差異,還真分不清他和女兒的衣服。
女兒不像女生。例如那頭短髮。或者她每天上班穿的那雙貌似尺寸較小的男士皮鞋。但女兒確實是女生。每個月總有一、兩天,妻會煎好一碗藥端進女兒房內。女兒蜷坐床沿,枕頭用力按在腹部,即便是正熱的夏天,仍然披披掛掛。偶爾一陣痛起來,女兒像被某種巨大外力綑綁,整個人遽然縮起,咬著牙卻仍有細細的嗚咽洩漏。他在外頭湊近虛掩的房門,自細縫窺望,看妻摟住女兒,看女兒有時痛得身心脆弱,窩在妻的胸口,看得自己茫茫發著慌。
妻說,女兒的體質遺傳自她。西醫的檢查做了,中醫的藥、推拿、針灸也都試了,仍然每月彷彿遭臨一場大病。妻說自己以前也是這般,「倒是生了她就好了。」妻苦笑,「這樣到底是好是壞呢。」
但這五十多天以來,倒沒見過女兒那樣難熬。在後陽台夾妥最後一隻襪子時,他忽地納悶,連那幾天暴增的廁所垃圾,還有浴洗後偶爾不慎滴沾的跡痕,也都未見。怎麼回事?身為一個將近六十歲,所有性經驗都是和妻一同發生的男性,念及自己的女兒似乎五十天以上都沒來生理期,他不免有些或重或輕的揣測。想著便踱到妻的房門,敲門,輕喚妻,試試把手,貼上門問起那碗端進女兒房內的藥是什麼配方。沒有回應。女孩子有時候身體失調也會這樣吧,他說。沒有回應。妳每個月都要煮給她吃的那四物雞,不太難吧?
沒有回應。他長吁一氣,轉進廚房翻找鍋子。一併也尋到常備的四物藥包和一盒冷凍肉塊。應該不難吧,他對著流理台上三樣東西發愣。冷凍雞肉盒邊隱隱化出一灘水,他的記憶渾糊,四處流淌,以前三個人圍著一鍋雞,尋常無話的時候,妻便喃喃念起這雞該怎麼燉。每一次的聲調和停頓都相同,他毫無留意,反正,下個月這雞仍是妻會料理的。水漫到他托著流理台邊緣的手,他索性拆掉盒子,生雞肉和藥包全丟進鍋裡,盛滿水便上爐子煮。
火烘得他雙頰發燙,汗濕衣領,一面撈浮沫,一面看著透明水漸漸暈黑。他從褲子口袋掏出手機,LINE,點按女兒的大頭貼。我煮四物雞,晚上回來吃吧。送出。女兒秒回,一張「okay」貼圖。貼圖小人貌似挺興奮的,他不確定女兒的表情為何,還想寫些什麼,輸入處的直線閃爍,心底閃過紛雜斷語。倏忽湯水大滾沸出鍋緣,爐火瞬熄,隨之白煙蒸騰,瓦斯味衝鼻,他忙地擱下手機。白煙消散時,他想起前天妻的照片燒起來是很濃很濃的,黑煙排空,順著向上望,夜晚的天空正如一鍋透明水漸漸暈黑。
燉一鍋雞,到底還是有些難吧,他拿捏不準,煮得骨肉分離。夏日傍晚七點的天空還殘著光,他全身褪得只剩一條四角內褲,盤坐餐桌一角,遠端望見玄關的窗戶框住墨藍的天,近則端詳和他垂直對坐的女兒,舀起黑黝黝湯水,瓢裡都是骨頭,牽掛零零散散碎肉。
今天據說是入夏最高溫,他和女兒分著吹電風扇,藍色扇葉轉向他,復擺過去,女兒上了一整天髮蠟的短髮,僵持不住,垂落幾綹晃蕩額前。女兒的短髮,削去兩側,僅留頂部,每天做不同造型。他曉得這是流行,路上的年輕人,作七和告別式見到的親戚晚輩,大多這副模樣。只不過,都是男孩子。女兒袒露的額頭沁出汗珠,他想起告別式那天,家屬列隊答謝,司儀囑咐男眾一邊女眾一邊,女兒跟在舅媽後頭,司儀又提高音量,男眾一邊女眾一邊,伸手向女兒示意。女兒仍然垂首,大抵還沒意會到司儀對著自己。終於司儀離開他的位置,走進女性家屬,拍拍女兒的肩,另手仍持麥克風,男眾一邊女眾一邊。
站列的家屬和排隊的外人,一雙雙浮腫的眼接連抬起,觀望這秩序之外的插曲。是漫淹的涕淚或空調不盛的會場,又或是祭儀翻騰起的濃濁思緒,家族眾人一時間都沒能反應過來,一些辯駁一些澄清,哽在喉頭。包括他自己。他正要上前,女兒卻一言不發,埋頭,從女眾那邊,承著所有人的目光,越過前台中央,達抵他身邊。他回過頭來,見她一滴汗自袒露的額際沁出,滑至眼角,一眨便滲入眼瞼,染紅眼眶。
女兒肯定委屈了。可他又想,覺得這事委屈或不委屈,哪一個對女兒才真是委屈呢?無論如何,總是不容易吧,女兒這樣子。
女兒這樣不容易,應該還會在家住上好些時日吧。這五十幾天,沒有妻徘徊於他和女兒之間,梭織兩人幾無交集的日常和近況,安靜便濃稠地滲進每個角落。總是女兒起得早,他起得晚,不喝咖啡的她會溫一壺咖啡給他;女兒常加班,回來得晚,他一日忙完瑣事,便早早睡去,睡前他會留紙條告訴她冰箱有什麼方便熱起來吃。他們在平日錯過作息,在假日沉默地錯身,偶爾會有今天這麼一天,他們無語對坐一餐。他有時揣想,日子是否就要這麼過下去了,一方屋簷,兩個人,各自獨居。
意識到這些,他忽然非常想見到妻,踅到妻房門外,一次又一次壓下不會動的門把。遠邊浮著女兒洗碗的水聲,手裡的門把碰碰撞撞,他焦急起來,彷彿被鎖著的是門外的自己。
他渾身浸滿門把的嗑碰,直到女兒喚他的聲音穿過他瞬間靜止的心搏。他驚詫回過身,擋住門把像藏著一個祕密,但其實他想告訴女兒這個祕密,妻回來了,不,如果是要和女兒說的話,應該是,妳媽回來了。五字堆擠喉頭,兩人視線交纏。
再一次,告別式那天一般,他正要說明什麼,女兒卻已垂下雙眼,離開那個話語梗塞,空氣繃至險些綻裂的現場。
七七之後一週,他一如往常醒得晚,房間蒸熱,空氣溽濕。拖起身子,開門,行經女兒房間,轉彎,浴室,客廳,女兒的拖鞋擺在玄關邊緣。這週下來,他已習慣每天起床巡視家中,確認沒人,再試試妻的房門把手。於是一如往常右轉,一手早已舉起,正要搭上門把。
卻探進空無。
妻的房門敞開。
他一時怔忡,佇立房外。這分明是他多日試探,隱約希望發生的事,但真發生了,反而有些虛惘。
或許因為仍沒見到妻吧。
謹慎步入,環視房內。一張單人床,床頭有矮置物櫃,床尾和梳妝台之間僅容一張座椅,梳妝台旁立一座組裝式衣櫃。五件家具幾乎填滿整個房間。他仔細檢視每個平面,置物櫃上的鬧鐘、乳液、護唇膏、眼藥水;床上摺疊好的棉被壓在枕頭上;梳妝台的鏡子蓋下去了,成為一個小小桌面,化妝品應該都在桌面下,桌邊只擺面紙、化妝棉和棉花棒;衣櫃關著。
房間沒變,像誰來過也像從沒住過誰,那便是妻的模樣和性格了:整潔,清淨,思緒和習慣都收納妥當,沒有明顯的生活跡痕,例如隨手掛在椅背上的衣服,或底處殘一口茶的杯子。妻的房間收拾得像家居用品展示間,任何人都能進來,沒有負擔地坐坐。
也隨時都能離開。念及此,他有些心驚。
當初決定分房是妻的意思。妻的更年期症狀犯得兇,他幾次夜半醒來發現妻跪在廁所裡嘔,沒有指責但十分哀怨說自己暈得厲害,他頻頻翻身她就像在暈船。這下連同他也睡不安穩,最後妻提議把儲藏室清空,權充她的臥室。一人睡雙人床,他還是只躺左半邊,是睡得舒坦了,只是偶爾翻向右側,一手伸過去卻探了個空,他會訕訕把手收回被窩,有些茫然想著,不知妻一個人睡得如何,平日妻一個人在家,又如何。只不過分房睡便覺得妻神祕起來。
或許妻的衣櫃藏了一件沒在他面前穿過的洋裝?還是掀開化妝桌會發現一個不是他送的墜子?像現在這樣獨占妻的房間,還是分房以來第一次,他大可打開衣櫃解答各種揣想。但他沒有,比起忖度將近兩個月不見的妻是否有過他不知曉的另一面,此時的他更加惶然,又一個禮拜過去了,還是沒見到女兒每個月如臨一場大病那樣虛弱的時刻。他坐在床沿,雙手向後撐,毛巾被搔得他有些不安。
許多念頭旋繞,在他心底膨脹,發酵,最後冷不防洩出一句,「妹妹好像兩個月沒來……那個了啊?」他措詞非常小心,小心到有些結巴,彷彿有誰正在傾聽。
他和妻叫女兒「妹妹」,好像女兒上頭還有兄姊似的。事實上,他們沒能來得及知道第一個懷上的孩子究竟是哥哥或是姊姊。妻還為此服過一陣抗憂鬱劑。那是他記憶所及妻唯一懈怠家務的時光,時常他回到家裡,屋內昏暗,他從玄關至主臥房一路開燈,每摁亮一盞便照見一些頹敗的軌跡。茶几上積滿一週的報紙和廣告傳單,浴廁薰著只有停水時才會有的惡臭,洗碗機胡亂堆著的仍是前天的碗盤。及至主臥房,他佇立房門外,還沒開燈就曉得裡面的情況。聲音比光更早砭刺過來,妻趴在雙人床旁空蕩的小嬰兒床,兀自哼著難辨的旋律,微風輕晃嬰兒床上的風鈴,各色卡通化動物懸空款擺,鈴聲碎在妻連日沒褪下過的睡衣。(待續)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