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吳鈞堯/他們的局
◎吳鈞堯
很多人不知道三重距離士林、故宮,以及東吳大學,都非常近。因為鮮少人知道一個市鎮的具體輪廓,就算落腳三重數十年,我也只知道它與蘆洲、五股、新莊比鄰,與北市隔著淡水河淡淡相望。說是淡,因為就是淡,非淡不可,一條河可以切隔的,除了地域還有貧富。
我曾經在鍾文音、花柏容以及陳又津的小說讀過舊三重;三重區寫作班學員也書寫他們的重重記憶,茉莉花田、三和夜市、大河氾濫、黑道挾藏扁鑽登門討債,以及分成三班、日夜輪轉的車床工廠;這是馬達不停運轉的城市,尤其愈往它的邊緣,工廠愈多。
我在90年代,於五華街、富福街一帶買了房,脫離父母所在的三和路、正義北路等傳統三重核心地帶,沒料到重陽橋通車以後,讓原本的三重邊陲成了士林的生活圈。我還記得住在富福街時,巷子裡頭有不少工廠,樓下住一位矮胖的先生,他的雙下巴每一年都更接近地面。他沒天沒夜地,或搥或磨或敲,把一個方整的玻璃,打造成橢圓的、圓的各款規格。
他不太跟我打招呼的,直到我搬到隔鄰的五華街,有次回家拿東西撞見了,問我好久不見,做什麼去了?
我沒換工作,依舊在出版社上班,但因為剛剛考上研究所,心裡頭惦著這事,以為人家問的是這事,便說,「考上東吳研究所了。」矮胖先生哦地一聲,仰起頭來看我一眼。這位不太搭理人的先生,心裡還是很藍領的,而讀所、在竹科上班等,很可能是他曾經做過的夢。彷彿那一聲「哦」,已是無比親切了,他快速回到工作崗位,蹲坐在一只暢亮的檯燈下,戴上老花眼鏡,捶打那些乾淨、漂亮、不沾塵埃的玻璃。
叩叩叩,扣扣扣……我往大廳看了幾眼。很可能是燈光反差,很可能是他的搥打非常搶戲,以致於他跟他的聲音,成為大廳唯一的一齣戲,我竟想不起來他的太太跟三個小孩,長什麼模樣。
這樣的錯覺很像我跟別人說,「真的啦,我家到故宮搭計程車不到十五分鐘,至於東吳大學,十分鐘就可以到了。」聽者都紛紛狐疑,心頭嘀咕,「騙肖仔,不如跟我說故宮搬到三重卡緊。」
極短的時間內,進出氣味不同的城市,它的翻轉很迷人。就讀東吳大學時,當夜間下課了,我常直截下樓,看接駁公車是否開走了?它開走也好,我才能匆忙趕路時,又問自己匆忙趕路做什麼呢?我只要慢上那麼一步,就能接收大學夜間的青春。操場燈光明亮,慢跑的人總是七、八位,不多不少,如同對弈的殘局,將、士、象、車、馬、砲以及兵跟卒,都各有安排。籃球在操場零星彈跳,男孩與女孩圍著彼此的紅顏,無論怎麼看,都與我非常遠了,但我很明白,有些事情就會莫名其妙地發生了。
我走出,到了沿河的紅磚道。路燈探不著每一道水流,耳朵接收不到每一滴喧譁,有時候與同學一起走,討論著報告、資格考以及回家後,要面對的不同家庭,我們都寧願這一條路,永遠不要走完。
我到士林再接駁另一班公車回家。運氣好,搭了同學便車,從外雙溪回返三重住家,匆匆三十分,匆匆好幾種轉境。我以為樓不高、房不大、路不寬是士林中正路的特徵,它非常本分,不是人人可以住進來,但是人人都能經過它。
假日,我與家人都愛踏青,陽明山、風櫃嘴以及大崙尾山都常往。經過東吳大學校門前,我提起有一、兩回,古籍校閱課程於週末上課,孩子且陪我安坐課堂,他是忘了,他更記得的是我應邀評審或演講,必得帶他同行,方便照料,他若是乖,會坐在第一排,若是耐性用乏了,便得坐到最後一排,我邊進行活動,還得偷眼瞄他,在喝什麼、吃什麼、玩什麼?我跟孩子說,人哪,不能一直坐台上,必須經常回到台下,上、下翻轉,眼界、心境才會跟著寬大。
我提起考所的糗事。消息不知何以走漏,有熱心朋友從台中寄來試題版中國文學史,上、下兩巨冊,心意濃重。更有朋友來函,說是單憑作文這一項足以讓我拉開差距,殊不知當我看到「論陶冶人才」,方覺論述本領早已失散多時,當一字一句都往情裡鑽的時候,它會讓思維愈靠近一個方向,但也更遠離另一個方向,孩子沒聽懂,我只好大方承認,「我那篇作文寫得糟透了。」我連帶地想起大學聯招時,我的作文題目是「論虛心」,寫完試卷,交換心得,竟有不少人誤寫成「論心虛」。
一個字的調轉,天差地遠,文字法門,一個字的差距,遠勝三重與故宮。
有一回上大崙尾山,收穫豐碩,看見台灣藍鵲成群飛過樹林,看見啄木鳥啄木,以及牠飛快爬升,垂直走踏,渾如武林高手。回程,翻轉幾個山頭之後,走上不知道名字的道路,道觀、佛寺修築於深山小徑,不少車友全副武裝,戴頭盔、著緊身排汗衣物,隨著路的起伏,讓風跟著起起伏伏。
最初,我們走進一座大宅裡,是因為妻子眼力好,看到桑葚紅得發黑,掉落一地,桑葚栽在宅院內,它結的果實似不屬人間了,任憑掉落。我們摘吃了幾枚,才發覺走進的宅院是「鄭成功廟」。廳堂內擺設空蕩,加上挑高設計,以及漸尖的屋頂,任何一個發聲,都要嗡嗡嗡、叩叩叩。
我吃一大驚。讀所六年,每回走進東吳大學,仰頭探看半山腰,都好奇那棟蓋得豪大、外觀氣派的建築到底是什麼?六年期間,我完成研究金門文學的碩論,慷慨激昂地述說金門工具化的命運,起自鄭成功占據金門廈門反清復明,二百多年後,國民政府建設金門為反共踏板,都愚弄了金門島民,我還寫了小說《遺神》,辯證鄭成功與金門的恩怨,這一切,鄭王爺都一一看入眼裡。
我彷彿誤踏陷阱,身陷敵境。還好鄭王爺並沒有叱眾,大喊威武。祂安坐,靜看前方。
前方,我出發的山腳、讀所六年所走的沿溪路、我在課堂上的每一個念頭,還有還有,當我於離聚人寰,執於一種茫茫,以及兩種茫茫。
後來,我回到屬於我的紅塵,依然我有很多的機會,從一個區域到另一個區域,在一種氣息裡,分辨另一株氣息。我常感到,我被誰盯看著,是殘局裡頭的那顆卒?曾經與我伴行的溪流?或者矮胖先生,在一個灰暗的廳堂,以一盞燈跟一支鎚,不停地叩叩叩?還有還有,那些骨溜、骨溜,日夜運作的車床,沖壓出一截截的鋼環跟鐵片,廠房的門口地板總是黝黑、油濘。
但有一回,我經過富福街,發覺廠房不見了。再往前走,就是不愛打招呼的矮胖先生跟他的家庭工廠。我猶豫著是否該往前走的時候,竟感覺到,我被他遠遠地盯看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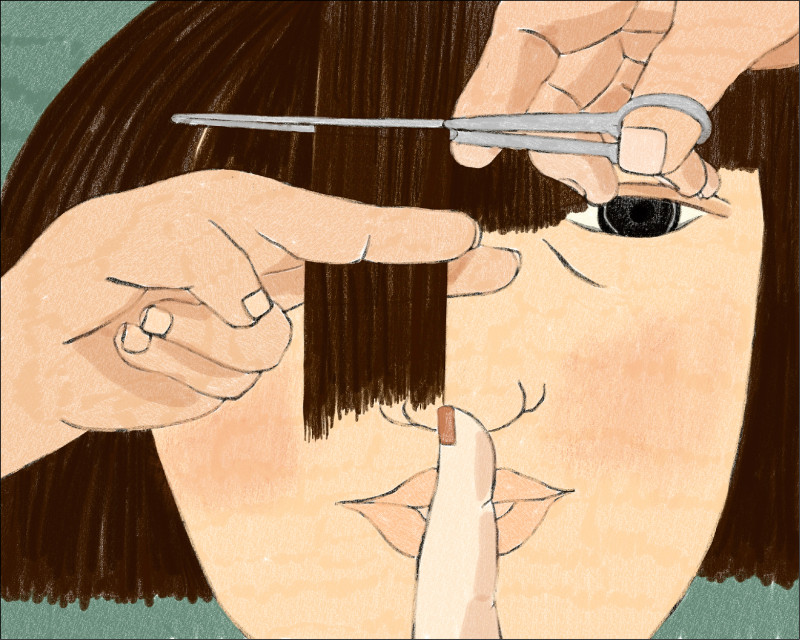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