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第十一屆林榮三文學獎.短篇小說獎二獎】3之1 - 雞婆要出嫁
 圖◎唐壽南
圖◎唐壽南
作者簡介:
 方清純
方清純
本名方瑞楊,雲林虎尾人,1984年生。文化大學俄文系,政治大學斯語所畢業。曾獲全國學生文學獎小說獎、桃園縣文藝創作獎小說獎。
得獎感言:
我很容易緊張,一緊張就會舌頭打結,接受編輯訪問就打個不停,若在台上致詞可能會打到天翻地覆,因此,得到二獎,或許是件好事,免在台上出醜。拿到這個獎,代表自己的寫作能力又往前一步,還有進步的空間,我會繼續加油的,謝謝。
★★★
◎方清純 圖◎唐壽南
雞婆一輩子都想著嫁人。白紗不要,要鳳冠霞帔,最好還有八人大轎來扛,長鞭炮竹劈里啪啦響,搞得風風光光。
雞婆不是雞,也不是婆,個性確實有點雞,模樣幾乎像個婆,拉開褲襠一看,不折不扣是帶把的。唉呦~~他尖叫著死不承認,把那玩意兒藏得緊緊的,想讓它就這麼不成一回事。
雞婆不想當雞,只想當個真正的婆,六十年老蓄著一頭長髮,蔓過腰際,不免招搖過市,他卻光明坦蕩,不怕礙了別人的眼,彷彿他天生就該是這個樣子。
「披頭散髮活像個女鬼!」人家罵他也不發怒,反倒喜孜孜,只因那個女字。
雞婆叫阿良,加上個女字,變成個阿娘,年歲日漸長,就成了老娘。老娘老想著嫁人,肖想了大半輩子,可惜這世註定無望,誰叫他偏是該娶人的那個。
阿良一輩子沒想過娶人,除非登徒子開竅,除非豬八戒附身,除非他鑽回娘胎再輪迴一次。輪迴啊輪迴,誰知又會輪迴成啥樣?真輪迴成女人,只怕又想娶人!我說倒不如輪迴成一隻雞,總比當個半人樣的雞婆強。
阿良當不成女人也不當雞,做雞做鴨無了時,做人較快活自在;就算真要當雞,也要當李家雞窩裡的,喔不,他羞赧地擺擺手,細聲改口說,他只想當李家阿財被窩裡的,伴,同枕眠,共偕老,生相依,死相隨,說完呵呵笑,笑成一隻三八雞。
雞婆滿頭烏髮,像隻黑鳳雞,儘管已屆耳順,猶然墨黑得恍若少年。有人說鐵定是用墨水染的,另一人反駁說墨水再怎麼染,總不會連髮根剛冒生出來的也全是黑的吧,難不成用喝的嗎?
阿良才不喝墨哩,他只吃墨……魚,渾身濃濃墨味,不是墨魚的墨,而是墨硯的墨。他寫得一手好字,書法隨手便成一帖,拿過國內外不少獎項,在地方上頗富名聲,順勢就開起了書法班。
阿良的絕活是用他那頭長髮揮墨,將髮尾束成一支大筆,蘸墨水在六尺全開宣紙上寫大字。有人碎嘴說阿良根本不必蘸墨,那頭烏髮沾沾水便能在紙上塗出墨來,我說他的髮囊異於常人能源源不絕分泌墨液,那人驚訝地張大嘴問是真的?!我說難道你以為只有你會鬼扯嗎?那人白我一眼,跟白目一樣白,白不過阿良手上那張白紙。
每當阿良一握筆,便像換了個人,這時他不是雞婆,而是個真正的漢子,出筆如出拳,剛柔並濟,虎虎生風,在紙上打出一道又一道太極,見識過這紙上功夫的莫不讚歎折服。
阿良的書法是自學的,頭髮留了多長,學的日子就有多長,嗯不,比他那頭長髮還要長得多呢。阿良打出生沒剪過幾次髮,把頂上三千煩惱絲看得比命還重要,要剪他髮不如直接剪斷他喉嚨。「剪掉命根子好了,正合他意!」多嘴的來一句,我立馬頂回去:「你舌頭怎麼不剪一剪!」
阿良的脾氣不算壞,就壞在一個倔字,從小就這麼倔,多半是對自己,對旁人倒還不至於,畢竟生為雞婆,顧慮都來不及了,哪敢胡亂招惹別人呢?
阿良自幼就是一頭及肩長髮,加上那清秀標緻的五官,模樣比他六個姊姊還漂亮,整村子的女孩包含我在內全都相形失色。阿良只跟女孩相好,男孩都把他當異類,玩他鬧他罵他查某體噁心死了扯他褲襠說要幫他割掉雞巴讓他當個真正的雞掰,這一胡鬧起來沒人插得了手,除了家裡開養雞場的阿財以外。
阿財長得不像雞,比較像牛頭馬面,一臉凶惡相,不過稍長阿良兩、三歲,塊頭卻超齡地又高又魁,活像個鍾馗,每次一顯靈,就把小鬼們嚇得鳥獸散,我猜多半是靠他那一身陳年雞屎味。
「阿財娶阿良,阿良嫁阿財,」一群男孩起鬨著亂湊合:「嫁給養雞的當老婆,變成個雞婆!」這下清楚了吧,雞婆就是這麼來的,既是他天生的本性,亦是旁人後起的名分。阿財根本沒當一回事,但阿良卻當真了,此後一輩子都惦掛著這個人。
雞婆啊雞婆,也不是真正的婆,帶把的終究賴不掉。阿良這頭髮留得再長,上中學也得理成顆平頭,但他寧死不屈,誰都拿他沒轍,不理也不上,後來還是買通人關說,才准了阿良帶髮就學。我說幸虧他生在富裕人家,否則哪容得下他這般執拗?
日子一天一天過,頭髮一寸一寸長,加上他身體病弱免役,躲過入伍那兩、三年的斷髮劫,一路就這麼留到長得幾乎能用來上吊,呸呸,這話我收回,長得幾乎能曬衣被掛肉腸給孩子當跳繩玩才對。阿良的長髮漂亮得教人羨妒,每個女人都想剪一把來添在頭上,只是可惜啊,若不是好幾年前為他父親裁過那麼一次,他那頭長髮現在都不知道長到什麼地步了呢!
村派出所對面是小學,小學後門隔條路建了一排透天厝,透天厝最底有間新式紅瓦平房,阿良的書法班就在那裡。
屋子是他修建的,二十坪大小,湊合湊合;土地是向人租賃的,一個月三千塊,意思意思。一進門,便見兩張長方桌,每桌各配六張椅,角落有個木櫃,放置文房四寶,牆上則掛滿了阿良的字畫。這裡既是學堂,也是住家,再往裡走,就是他的臥房,房內雅潔有序,滿溢女人家生活氣息。
自阿良五十歲那年返鄉,便在這裡落戶成家至今。老家明明近在咫尺,他卻執意一人,怎麼也不肯回去。真是怪哉!阿良他家可是望族呢,光田產就有十幾甲,鎮上還有數爿店面出租,行庫裡的積蓄就不消多說了,全都歸在他這獨子的名下,但他卻一副毫不貪戀的模樣。
「有錢才能裝清高啊!」有人酸溜溜道。「反正富也富不過三代!」貧嘴總是酸溜溜。有時怕的倒非富不過,而是不過三代,傳宗接代的代。雞婆只想著嫁人,傳不了宗,也接不了代。
外人不明就裡,大概誤以為阿良與雙親因香火之事有了嫌隙,才使他返家不得。我得說他父母可從未嫌過他,雖說按照一般通俗劇裡的發展,他父親理當大發雷霆,將這雞婆兒子趕出家門就此斷絕關係才是,但人生的劇本哪可能真照你的意思走,他父母非但不嫌棄,還分外地疼惜他呢,只因四個字,心懷愧疚,愧於把他生成個雞婆,疚於讓他一輩子受委屈。
阿良一輩子都不委屈,倒是怕家人因他而委屈。「所以你才逃得那麼遠?」我說。他笑著答道:「也不是逃,只是不知不覺就走遠了。」「繞了一大圈,還不是又回到這裡。」「是呀,不然是要去哪?」「天涯,海角。」「好一個天涯海角,改日咱結伴作伙去。」「哼,和我去?你是想跟心上人逗陣去吧!」「哎呀,恁祖媽的心思都讓妳看了了啦!」阿良掩面裝害臊,只是不知那手心裡捧著的,是笑臉還是苦臉?儘管他滿心盼望,一輩子終究走不到這條路上去,畢竟,他跟阿財又不是同路人。
阿良的書法班多在週末授課,好配合學生們的時間。平日裡,除了晚上幾堂零散的長青班,白天幾乎無人光顧;其時若有人路經此處,常常只見屋內兩張大桌合併,上面鋪展一張兩人長的宣紙,屋裡的人倚牆或站或坐,凝神專注於潔白的紙面,彷彿那裡頭藏著什麼天大的玄機,往往看著看著,一天便這麼過去了。
十年如一日,一日卻始終未得一筆,紙上空白依舊。「你到底想寫什麼?」這話我問了上百次,大概在第幾百不知哪次的時候,他終於回答了:「寫……人生。」「那怎麼不下筆?」「不知道要寫什麼。」「拜託哩,琢磨十年了吶,還不知道!」「再過幾個十年都一樣,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就算過完一輩子也不見得知道。」
我不知道他在不知道什麼,他的不知道讓我更加不知道起來。「你是想寫個大字呢?還是想寫串句子?或者,造首詩詞?」「嗯……不知道。」「你再給我不知道試試看!」「我是真的不知道。」「你,你就一輩子這樣不知道下去吧!」我沒來由地怒火中燒,搞得他莫名其妙,我也摸不著頭腦,大概更年期作祟,二話不說,直接回小學上課去。
我任教的小學沒書法課,一堂也沒有,這年代的教育不時興這種老古董,多數父母也不想讓孩子走回頭路。「都已經是原子筆的時代了,還拿什麼毛筆?連原子筆也快淘汰了,現在都用電腦打字哪,學什麼老掉牙書法!」因此,會到阿良那裡學書法的,真的是少數中的少數,少到連餬口飯都快餬不下去了。
「時代變了,變得愈來愈快,再也慢不下來了。」阿良悵惘地說,說得那樣慢,慢到彷彿整個世界都把他拋在後頭了。他慢悠悠地將紙攤開,慢騰騰地把墨磨好,再慢條斯理地下筆書寫,一筆一畫竟那麼艱難,那麼猶豫,愈寫,愈,慢,再慢下去,一輩子都要過完了。
「一輩子,用一張紙寫,算少還是算多?」阿良自言自語地說。他時常說些教人不知該如何應答的話。我叫他別一直鑽牛角尖,還是來學校幫忙指導學生吧,挑一、兩個書法寫得不差的,加強訓練一下,好參加全縣中小學書法比賽。
「比賽?沒有書法課,卻有書法比賽?」「別問我,上面的人搞的。」「搞?搞什麼!?」「大概書法課礙事,書法比賽不礙事吧?」「不教不學,是要比什麼賽?」「說是比賽,其實不過就是湊個數,好有個交代罷了。」「湊數?揀學生去湊數?」阿良輕撥臉上的髮綹,微慍地哼了一聲說:「真不像話!」他嗅聞髮上的墨味,似笑非笑,一副不以為然的樣子。
阿良的生活是黑白的,墨水的黑,宣紙的白,身上的服裝同樣黑白分明,像是要襯托身分似的,一身改良式的唐裝,素色內衫,緇色外衣,加上一條黑長褲,連鞋子也是一款的。
阿良的黑白人生只在晝日,一到夜晚便綴滿繽紛色彩。他的衣櫃裡掛滿各式女裝:紫色短熱褲,靛藍色旗袍,青綠色洋裝,橙黃色連身裙……還有,一件大紅色的嫁衣。每夜就寢前,他總要將嫁衣穿在身上,讓鏡子映照出一個待嫁紅娘,一個只活在他妄想裡的女人的形貌。
那女人面塗紅妝,一臉羞澀樣,恍若未經人事,嬌嫩如蓓蕾。他緊盯著女人的面容,看得心馳神往,真是難得啊,在外頭打滾了那麼多年,一路上也跟不少人廝混過一段,沒想到竟還能保有貞潔的一面,胸口不禁一陣沸騰,一半是感激,一半是感慨。她眼中漾起水光,他伸手揩去淚痕;他為她心疼,她為他心酸。
「藍色的街燈,明滅在街頭。獨自對窗,凝望月色,星星在閃耀,」阿良輕輕吟唱老歌,歌聲寂寥悽切,正如他此刻的心聲:「我在流淚,我在流淚,沒人知道我……」
阿良只在人後哭,人前總是笑吟吟,就連老父過世時,也沒讓外人窺見一滴淚。我說何必那麼倔?他說這是骨氣,不讓人看輕的骨氣。阿良外表娘聲娘氣,內底倒是男子氣概十足,跟他的書法風格一樣,遒勁不纖弱。
「沒人會看輕你的。」我真想這麼對他說,話卻鯁在喉頭,讓我一時啞口。雞婆怎可能不被看輕呢?一言一行都落人話柄。口氣太媚,步伐太騷,模樣太雞,怎樣都有話說,說得好似他是人頭雞身的怪物一樣,一旦他跟哪家男人走太近,便開始胡亂謠傳哪戶要得雞瘟啦!「講吧,隨他們去講吧。」阿良神情淡然,無畏人言。不管誰人笑話他,他都不嗔不怒,學聲母雞咯咯叫,自娛娛人也愚人。「要造口業隨他們造,下輩子換他們去當雞!」
阿財的養雞場就有一大群,恐怕全是上輩子造業作孽的下場。阿財養的是白肉雞,羽毛潔白如紙,彷彿隨時等著阿良來題字似的。養雞場藏在村落平房堆裡,外地人若欲尋門路,只消引耳探聽,雞啼最響亮處便是。阿良三天兩頭往養雞場跑,不是把自己當雞,而是為了那養雞的人。
阿良和阿財天差地別,個性一柔一剛,長相一白一黑,彷彿陰陽兩極。「天曉得這兩人怎會搭在一塊?」老有人這麼說,說了幾十年了,還是照說。兩人身家背景相殊,人生際遇各異,本該搭都搭不上,有緣搭上了,情誼便維繫數十年,從不為他人訛語所挑撥。阿財三十歲娶妻時,阿良幫忙備事迎親;阿良五十歲失怙時,阿財幫忙治喪送終,一路相挺互扶持,親愛得好比同血同脈的骨肉。
「換帖兄弟嘛,又不是當假的!」阿財總說得篤定,阿良卻悵然低語:「換帖,兄,弟……」說得聲聲慢,一聲慢過一生。在阿財眼中,阿良不過這般關係,但在阿良心裡,阿財可不只四字如此。(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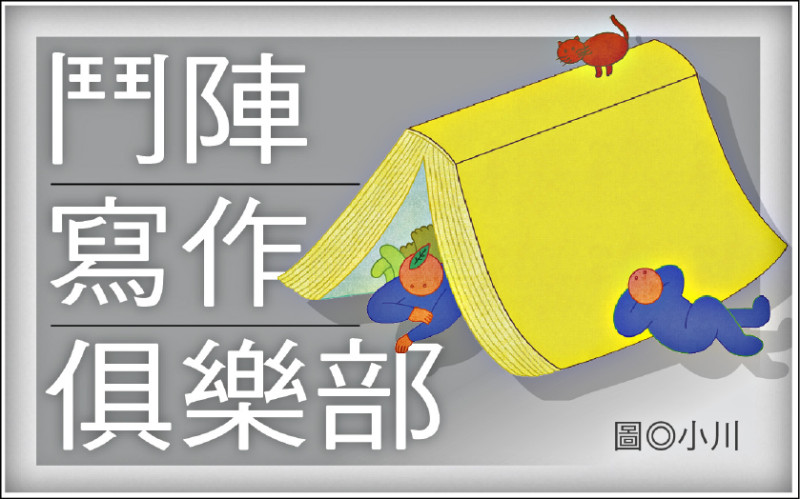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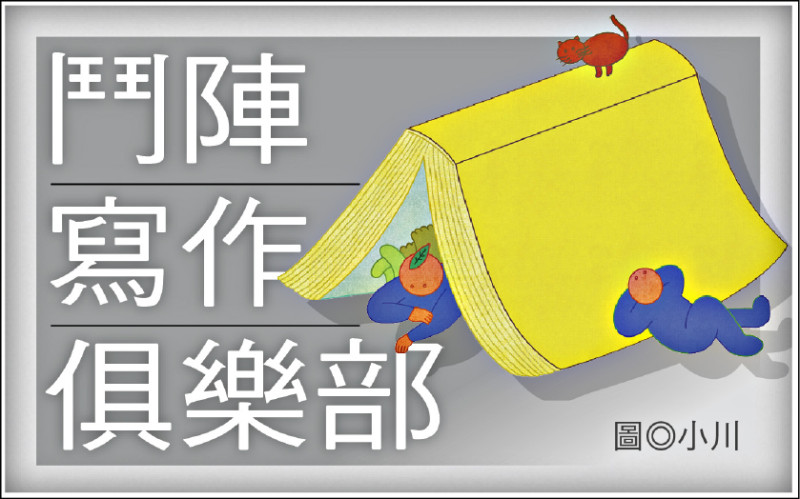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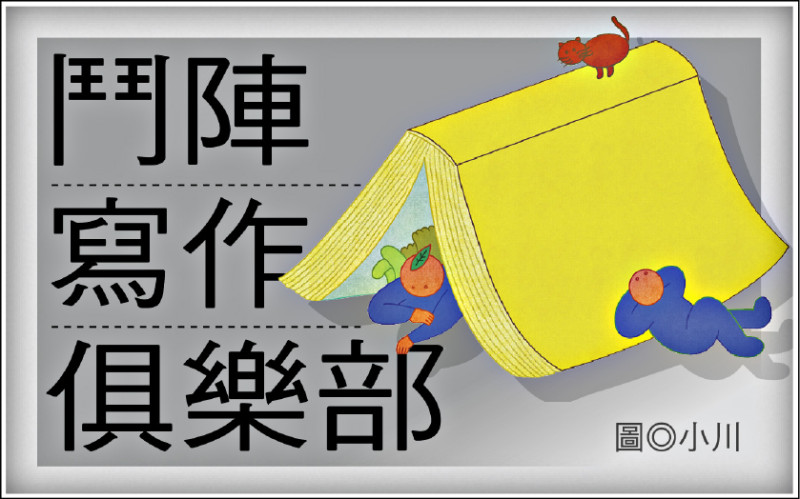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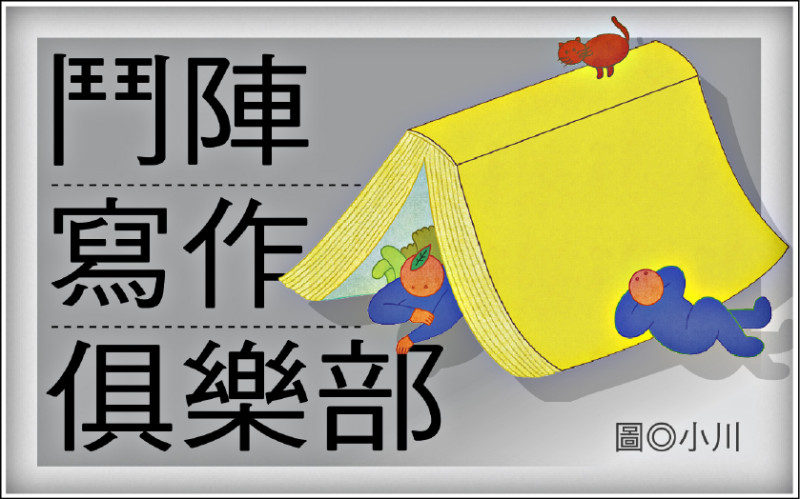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