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柏林的昨天
 1970年前西德總理勃蘭特在波蘭華沙的猶太人殉難紀念碑前下跪的歷史鏡頭,仍在大道上的櫥窗後,提醒著歷史的憾恨。
1970年前西德總理勃蘭特在波蘭華沙的猶太人殉難紀念碑前下跪的歷史鏡頭,仍在大道上的櫥窗後,提醒著歷史的憾恨。
文.攝影◎廖志峰
 每天跳上S線火車,走訪老城區,幾乎都在過去的東柏林範圍遊蕩。不過,西柏林還是保有片段的歷史遺澤,像這月台上的美麗磚牆。
每天跳上S線火車,走訪老城區,幾乎都在過去的東柏林範圍遊蕩。不過,西柏林還是保有片段的歷史遺澤,像這月台上的美麗磚牆。
在一座城市中不辨方向,這說明不了什麼。但在一座城市中使自己迷失,就像迷失在森林中,卻需要訓練。──班雅明
 來不及排隊進去參觀德國國會大廈,只好在外圍的樹下瞻望,感受秋光,卻也怡然自得。
來不及排隊進去參觀德國國會大廈,只好在外圍的樹下瞻望,感受秋光,卻也怡然自得。
接到客居柏林的中國流亡作家廖亦武來信,他獲得2012年德國書商和平獎,問我想不想去參加他的頒獎典禮?這真是一件盛事,從來沒想到我認識的作者中,會有人得到這項國際大獎的殊榮,突然興奮了起來。剛好也可趁這個機會造訪從沒到過的柏林,順便見識一下他住的柏林文學之家,到底是什麼樣子。我不知道德國人是不是都這麼好客,不過,看起來廖亦武在這裡如魚得水,廣受歡迎。他脫離了中國底層作家的泥淖,翻出了國籬,居然進入德國/歐洲的文學圈,誰想得到呢?
 小丘陵般的空墓塚,有如灰色的矩陣迷宮,這是由猶太設計師設計的柏林猶太受難紀念區,就位在布蘭登堡門旁,具現著德國對罪行的懺悔。
小丘陵般的空墓塚,有如灰色的矩陣迷宮,這是由猶太設計師設計的柏林猶太受難紀念區,就位在布蘭登堡門旁,具現著德國對罪行的懺悔。
尋找隱藏的文本
清晨在法蘭克福入境德國之後,我搭乘火車前往柏林。不知為什麼,喜歡藉著火車觀看風景,火車總讓人感到一種安慰。風景剛開始時是新鮮的,但後來視覺就麻痺了,但還是警覺著,深怕錯過下車站次,柏林不是列車的終點站。五個多小時的車程,抵達柏林時,天氣陰沉,飄著雨絲,像是台北的早冬。車站出乎意料地壯闊,新穎,但又出奇地安靜,你不能想像這樣一座安靜的世界級車站,連台北車站都遠比它喧譁、熱鬧得多。我拿出了事先印出的指示,開始找路:「從法蘭克福上火車,到柏林總火車站下,我來接你。萬一大海茫茫,等等,就搭S5或S7地上鐵,從柏林總火車站到動物園(ZOO)下,走向西柏林鼎鼎大名的褲檔大街,我就住在附近,到時候再電話確定一下。能不能再帶五本《地震瘋人院》給我?五本太重,三本也行。太他媽的忙了,暫時寫這些。老廖。」
簡潔得像皇帝手諭。我很快地找到S線地上鐵,但在自動售票機前盯著都是德文的操作指示,不知如何買票,排在我後面的一位中年男子看不下去了,直接把我的歐元抽走,簡單地問了一下,幫我買票,我連操作都沒看清楚,就有四張車票在手,真是友善的城市。我在目的地動物園站下車後,才發覺鼎鼎大名的褲襠大街,很多在地人不知道確實方向,我問年紀大一點的老翁老嫗,他們不會說英文,我出示地址,他們也不知,東西南北地比畫一通。我後來改問年輕一點的朋友,很多是遊客,就這樣,我拖著行李箱在街道轉圈,幾乎花了兩個小時,終於找到這條大名鼎鼎的街時,外套有點濕,內衣也因汗濕透了,身體微微地起了寒顫。這條街的入口在大馬路邊上的一個圓環後方,剛巧道路施工,路口的推土機把路標擋住了,我來回經過兩次,都沒注意,我以為既然稱做大街,那麼至少要和大馬路交會吧。終於抵達了,另一個問題來了,我發覺我站在一棟大樓前,突然不知要按哪一戶的門鈴?我拿到的地址只有門牌號碼,沒有樓別,我想像的柏林文學之家是棟獨立屋,有自己的門禁和庭園,但完全不是這回事。再一次,作者的簡單指示有意無意地略過關鍵訊息,就好像隱藏的文本,我還是沒有從過去得到足夠的教訓。
柏林文學之家所擁有的這套房子,雖然位在大街之中,但十分安靜,有著挑高寬敞的起居室和兩間不下於起居室的大臥室,以及獨立的廚房,後來我待在廚房和廖亦武說話的時間最長。餐廳和廚房連在一起,廖亦武為了表達熱烈的歡迎之意,親手下廚,不論下菜,快炒,起鍋,身手俐落,完全是大廚架式。雖然住在德國,廖亦武還是大把大把地使用花椒和辣油,川菜的全球移動。在柏林的每頓晚飯都我讓吃得涕泗橫流,感動著他的熱情,佩服著他的手藝,但實在是太辣了,嗆到時想喝口水,只找得到白酒,非常想念台灣啤酒。
廖亦武的晚間餐桌,經常是從晚上6點開始,一直到12點結束,讓我精疲力盡,這不是我想像的旅程。吃著,喝著,聊著,配著濃濃的鄉愁,經常還吹起簫和彈撥拇指琴,酒後的廖亦武,話不是太多,說話很慢,心緒翻湧時,就讓音樂從指間、唇間流出,宣露他鄉異國的漂泊心情。我喜歡這個時候的廖亦武,柔軟一些,卸下心防地與人交流,他總在音樂中回到了成都或蒼山。在柏林的每晚,都是相同的節目,相同的結束。我對他的心情有點複雜,他有時單純,有時難搞,有時讓你啼笑皆非。有一次,下午突然下起短暫的大雨,然後太陽又露出了臉,可喜的秋陽,我居然在柏林看到異國的彩虹,正感動著時,手機突然震動起來,傳進了一條簡訊:趕快回來,有事討論,老廖。不知發生了什麼大事,顧不得難得的金秋風景,匆匆跳上火車,趕回宿處,一進門就問他怎麼了,他竟說:沒啥事,就幾個朋友要來,讓你回來一起吃飯。我在柏林的夜晚其實平淡無奇,如果還有更特別的經歷,那就是晚上睡覺時,有時可以感覺到突然走近身邊的腳步聲,但好像也沒有什麼惡意。我不知廖亦武有沒有感覺過那腳步?或者是睡死了――在另一個房間?有一次,我把這事告訴長住柏林的育立,他只笑笑說︰你住的是百年老屋,也許只是有人回來看看。我其實也不確定是不是幻聽,可能只是夜太靜了。
流亡者的交會點
廖亦武的宿處勾起我對班雅明的懸念,我對柏林的印象來自於班雅明所著的《柏林童年》。廖亦武說他住在大名鼎鼎的褲襠大街並不為過,一代哲人班雅明就出生在柏林西區的褲襠街附近,不過,在柏林的幾天中,並沒有去探訪班雅明的舊居,也許早已在戰火中夷為平地。這站的站名是「動物園」,真有一座從19世紀中期就建置的動物園。這座動物園也出現在班雅明的書中,他回憶童年的動物園,記憶最深刻的動物是水獺,水獺住在園中偏僻的一角,是「先知先覺的角落,是一切尚未來臨的事物,彷彿都已成過去」的角落。他還說水獺是雨水的聖獸,因雨而生,而存在,有意思的是,他把喜雨的自己和水獺這神祕的獨居獸等同了起來。
〈水獺〉是班雅明書中直接描述動物園的文字,藉著描述童年的動物園,也自況自己居於一個所謂先知先覺的角落。寫這本書時他已開始流亡,帶著一種永遠回不去的預感,敘述著童年的生活點滴,他少見的抒情文字竟帶有一股普魯斯特往事追憶般的甜美與悼亡腔調。《柏林童年》的書稿出土,就像是一部失傳已久的武功祕笈現世,1940年,藏在巴黎的國家圖書館中,直到1981年才被人發現,又直到2003年才有台灣中文版的問世。班雅明可能在寫作《論歷史的概念》時同步改寫了《柏林記事》,完成此書,順手藏在圖書館中,然後繼續逃亡,這一年底,他在西班牙的邊界小鎮波港自殺,越不過的人生臨界。《柏林童年》應該是他的絕命書吧,最後,也是最初的人生告白。
我不知歷史的概念究竟是什麼,反諷嗎?班雅明從柏林展開他逃離納粹,亡命天涯的旅程:中國作家廖亦武卻從中國出亡,來到柏林落腳,兩個流亡的人,背負不同的命運,他們的交集就在這條大名鼎鼎的褲襠街,一個應劫去國,一個應運而居,歷史的嘲弄。我直到離開柏林的那天,還是沒有去找班雅明的故居,每天幾乎都帶著前一夜的酒意醒來,以及微微的頭疼:也來不及去探望水獺,水獺也許已繁衍了幾代,或早已絕跡如班雅明。我對柏林的初步印象和傷感,基本上是環繞著班雅明而展開,廖亦武每夜的簫聲中,其實傳遞著和班雅明寫書時同樣的心情:深居國外的我開始明白,我即將和自己出生的那個城市,做長久的、甚至是永久的告別。
我離開了柏林,感覺離班雅明又近了一些,下次來,會記得去看水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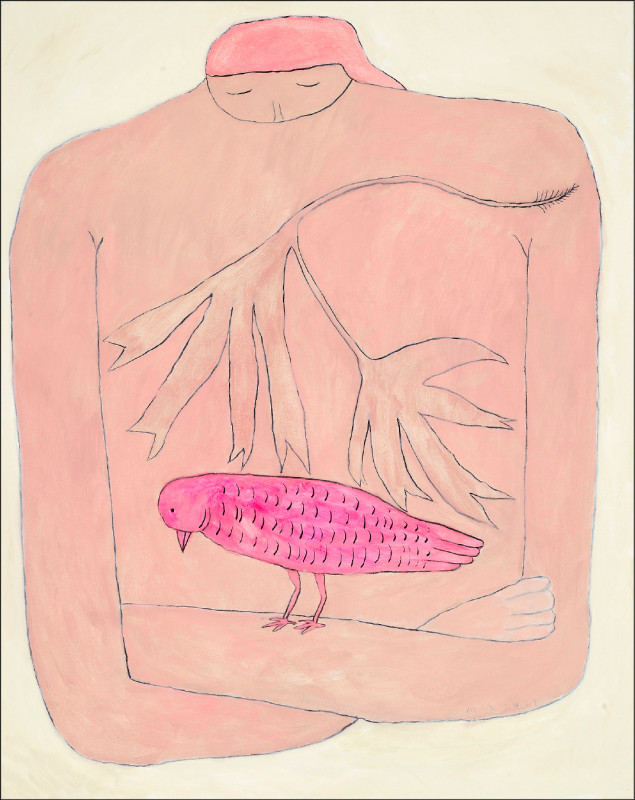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