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在邊緣
◎黃錦樹 圖◎黃子欽
十年前一個偶然的機緣讓我來到這裡。那時新婚不久,在台灣補請師友,聯繫一位多年前大學時代的老師,他人沒來,倒是客氣地回了封信(更多的大學時代的老師是置之不理,大概對紅色炸彈深惡痛絕。但不寄又怕得罪),說已畫好一幅畫要給我們當賀禮云云。那時在念博士班,需要工作,遂給幾間新成立的大學寄履歷,不料剛成立的暨大中文所有回應,正是那位昔日的老師,原來又是他到此地「創設系所」(台灣中南部國立大學的相關系所,一般都由北部幾間老國立大學「繁殖」而來──派一位資深教授去創設,不免帶去若干忠心的弟子門生,及衍生出相關的人情,同時製造出頗具勢力的學閥)。經過一番波折(主要是等待確認,譬如關鍵的聘書),我們就把全部家當(包括一輛畢業離境的兄長送的原本要報廢的破機車)搬進這小山城,匆匆住進打鐵街附近窄巷育樂路的房子裡。巷子窄到車子進不去,兩對戶人家各自停了機車腳踏車,放了納涼的竹椅後,就只剩一條散發著臭味的小水溝的寬度。屋內幾乎照不到太陽,如此的迫仄,被鄰居干擾也是必然的事。
剛開始根本找不到學校。問了方向,騎著那台聲音沉悶、吐著臭煙,逢雨必死火的破野狼(後來在一個寒冷的冬天,因暴斃而被棄置於龍潭暗巷裡)依著大指標(那時標示不清)在中潭公路上往返飆三趟都沒有發現學校的所在。原來那時入口新開了路,整片山坡剝了皮似的紅土裸露,部分在植草,圍網做擋土牆,難以形容的猙獰,竟沒想到那即是我苦尋不著的工作地點。原是一片台糖的牧場,一座台地,滿覆牧草,放牧著肉牛。破野狼確是噴了許多煙才走上去,寥寥幾棟建築,行政大樓,教室,學生宿舍,及我那時還沒資格申請的老師宿舍。
第一份正職,終於有第一份固定的薪水,身分也由學生轉為外聘,二十九歲了,發胖,掉髮。
兩年的講師,終究被淌進學院政治的混水,痛苦不堪,一言難盡。譬如終於理解年輕學者的銳氣和雄心是如何被磨蝕掉的;沒有才能而有野心的人占據了權力的位子會做些什麼事(據說賀爾蒙的分泌也會跟著改變)……而我那位資質絕佳(據說身懷書畫絕技)、古典訓練完備的老師,也充分顯露出他人格上及行政上的種種闕失──過分的大家長氣息,權謀,喜小朝廷。殘存的敬意及師生之誼,兩年內也幾乎消耗殆盡。但我畢竟該感激他(不論是無心還是有意的扶助),因彼時已鮮少學校聘用博士生為專任講師,因為量產的博士早已滿街跑。甚至我之被延攬,也有兩種說法。一是後來從旁人那裡聽到的,他是借我來保送他的一位同時聘為專任教師但只具有碩士學位的學生(此姝確實資質頗佳,傳統訓練也完整),他那時要求我需辦妥博士候選人資格證明;而(傳聞)他在教評會上推薦我的說詞即為第一種說法──那時我剛獲「時報文學獎」不久,出版了一本小說,發表了幾篇論文──「在座有哪位博士班還沒畢業就有這樣的成績?」也許兩種說法都成立,畢竟二者並不衝突,聘我不過是順水推舟,一舉兩得,或數得。
我也明確知道(有一陣子經常有不得不去的飯局,聊大小事)他鄙視資質與學問平庸之輩(這種人到處都是,且往往不知自量),只要是聰明人,即使那是敵人也抱有幾分惋惜的敬意。但我也惋惜他可惜太膽小,或受限於中文系窄仄的訓練,並沒有善用他的資質和學養,開啟有力的論說。我的另一位老師,他的同輩,曾多次讚歎他的聰明和學問,認為他是同輩中文學界最聰明的兩個人之一。最愛舉這麼一個例子──後來貴為中研院院士,及普遍被學界唾棄的那位綠朝新貴中國上古史專家,年輕時與他為鄰,因不諳上古文字,時時抱著上古文獻敲門請益,他也不需工具書,就地解說,傳為佳話。
猶記大學時代,此君以口才佳頭腦清楚學識淵博而普受「桃李」(大部分都是朽木吧)仰慕不已。而有一回我私下問他專長領域,他臉露忍著一半的笑意,慢條斯理地從上古文獻屈指數到清代,我也忘了其時他有限的、帶著粉筆灰的手指有沒有重複使用;另一回我拿著一本台北文化狂人李敖的《千秋評論》「王國維之死」專號,他無聊地翻翻,竟拿去揮打教室裡紛飛的台大蚊子,然後說了個故事。他說多年前他念研究所剛搬進台大男生宿舍,有一個人剛打包搬走,那個人就是李某。還說李敖很聰明,「和我差不多。」我也覺得這並非虛言,先天的稟賦就像是上帝擲的骰子。
只可惜終於消耗於各式各樣的自我內耗,尤其是性格上的扭曲。是因為有著不為人知的精神分析意義上的身世的創傷?還是偏安戒嚴體制下的老中文系早已患病──是癥候也是病院──消耗了良材?而問題或許也不僅僅是流亡者的文化守夜終成「乾嘉餘孽」?這都有待社會病理學家研究。
大概真的「涉世未深」,總是不解,不是教育的場所嗎?為什麼那麼多人都對權力看不開,視學界如政界。必須經過幾年的紛擾與角力,「權力平衡」後,方能漸漸平靜下來。
三個月後搬到明德路,兩層的排樓,養貓三隻;又一年搬到隆生路,埔里盆地邊郊,半座三合院,妻最愛的荒廢老宅;父亡於故鄉,生子一,輕度腦溢血。年餘,搬虎山,台灣地理中心旁。遇大地震,幸房子堅固。
貓失其一,流亡北部半年,生女一。
遷學校宿舍,貓又失其一,住三年。
遷牛尾,盆地另一處邊郊的大農舍,迄今又近兩年,老貓失其一,又失一黑貓。新養小貓三隻,小雞三隻,烏龜二。
住在這樣的地方,多少有點隱居的感覺,至少遠離多交際應酬的大都會。往來的文壇朋友並不多,外頭的活動能不去就不去,恪行一動不如一靜。無疑我是此間文壇的邊緣人。就這點而言,和兩位來自熱帶的同鄉小說前輩倒是一脈相承。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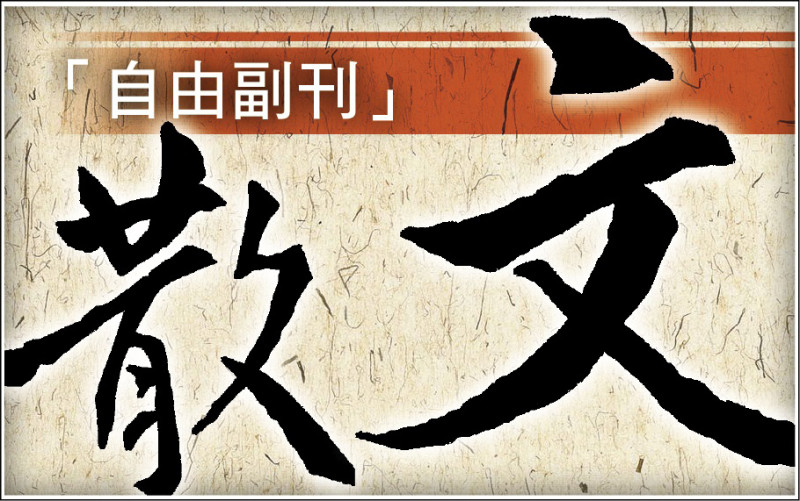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