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第十一屆林榮三文學獎.散文獎佳作】 蚵牙少年
 圖◎吳怡欣
圖◎吳怡欣
【作者簡介】
 ◎顏訥
◎顏訥
顏訥,1985年來到世界上,台北與花蓮都是故鄉。清大中文所博士生,文學打工仔,寫散文也寫評論。在UDN鳴人堂與Bios Monthly有兩個寫很慢,愧對編輯的專欄。
【得獎感言】
學會與恐懼共存,這是寫作教我的事。謝謝一路上拉住我的朋友,要我停下來,更安靜地寫。謝謝爸爸出借身世,讓我看見島嶼下沉上升的軌跡。一整個世代的遷徙者,都是半人,格格不入,又融入得太努力,希望我能在離完人永遠的最後一哩路上,寫好寫滿。
★★★
◎顏訥 圖◎吳怡欣
少年父親上台北以後,決心換一付新嘴巴。
舊的嘴巴被太陽漬得黎黑,肥肥兩瓣,掛在臉上像冬日裡剛煎香上桌的烏魚子。一咧開嘴哈哈笑,兩顆大門牙就蹦躂出來,不仔細看,還以為嘴裡含著翻出白肚皮的鮮蚵仔。村裡姓顏的人都有這種蚵仔門牙,倘若一家好幾口手勾手列隊沖著你笑,藍天白雲青灰海浪之間,那便是一喇又一喇的蚵田風景。
從蚵仔門牙邊磨擦出的字都是鹹的,沉甸甸,揪緊尾音一路向下,眼看與正在上升的話頭對撞,馬上又能一個旋身,後出轉精,妥妥把昂揚的語調接上。
少年父親移出嘉義小漁村之前,以為整個島的嘴巴都是那樣說話。
本來那樣說話其實好極了,在一張嘴整匹海風都往嘴裡灌的鹽分地帶,濃度不夠高的聲音,大概注定在表詞達意前就被吹得魂飛魄散。他特別喜歡以「逆」作結的問句,例如,汝是北七逆?問號的背後粘著一顆霸道的句號,讓人未有答辯的機會,只能默默把整頂帽子扣上:我是北七,謝謝指教。
這是逆的力量。以意逆志,逆向操作,方能逆轉勝。國小課本還讀過蔣公溪邊看魚逆水而上,汝是北七逆?當然,少年父親那個年代,以上二句中間如果放顆逗點讓彼此互涉的話,那可是大逆不道。
海口人話是鹹的,海口村的田地也是鹹的。「人肉鹹鹹,會勿食得」,討債碰壁自認倒楣的時候,村人習慣摸摸額頭歎氣,倒不是自慰的阿Q精神,而是給自己留一點餘地,人生沒辦法的事太多,總得在沒辦法中尋出辦法吧。可是,老天不怕食人肉,祂既能生養你,也能隨時奪你性命。40年代的嘉義漁村並沒有給人太多生存餘地,若不是田產本來就豐厚的家庭,單單只是活下去,也幾乎成為不可能的任務。
少年父親的阿爸就經常煩惱與活著有關的事情。
長年憂煩與飢餓讓他枯瘦到像一條無水可擰的舊抹布,也不只是瘦,還無比安靜,你再擰他個半圈,也擠不出三兩句話。那個年代,村裡男人大都安靜,那不是對命運無聲的指控,他們只是疲累,無話可說罷了。少年父親的阿爸明白,守著兩分鹽漬的田地,遠遠不夠餵飽一家六口。地瓜還勉強能夠生長,希望則是早早就在乾土裡死去。沒有米的海口歲月,何不食魚肉?當然,他也出海捕魚,無奈日日巡過的那片海洋一如岸上貧瘠,吐不出幾尾收穫。
於是,少年父親與弟妹們老是餓,飢餓的感受逐漸嚼光他整個童年。「桌頂食飯,桌跤放屎」,是罵人忘恩負義的俚語;可是,顏家的桌上無飯可食,生黴的番薯籤,遠觀近看都像萬頭攢動的黑蛆。下了桌更是無屎可拉,乾乾的羊大便粒粒皆辛苦,讓他們對生活滋養不出感激之情。
生活艱困如此,離開才有活路。
少年父親沉默的阿爸終於沉默地下定決心,等不了孩子們長大,就放下漁網,隻身到台北重開戰場。其實,50年代末,沿著台灣海峽鋪展開來的海線小村,還有許許多多個沉默的阿爸,踩在一毛不拔的土地上,做著沒有回饋的勞動。
夏季熱,中台灣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想及家中那一張永遠有欠缺的飯桌,一如妻子、孩子們在他踏進家門時望出去的眼神,做為一個總是無法令人滿足的男人,心底就有烈火燒灼著。於是,台灣中部海口的阿爸們,口耳相傳、摸石頭過河,一個拉一個往都市求生去。找頭路養家者有之,賭博躲債者有之,有的搬到台北,有的遷到高雄。西線漁村有戰事,然而,北上南下討生活,也只是換個戰場打鬥,誰也不能保證生活從此就不再有缺憾。
少年父親的阿爸來到台北,與其他都市討海人一樣,扔下鋤頭、漁網後,拾起現代化工具,努力加入城市中正要起飛的新興勞動產業。在台灣逐漸被鍍成金銀島的年代裡,等在鄉下的孩子們瞬間有了每個月固定寄錢回家的成衣廠阿爸、製皮廠阿爸、鋸木廠阿爸、五金車床阿爸,那些他們難以想像,聽起來比捕魚種田瞎趴多了的職業,逐漸讓餐桌上有了比較豐饒的景象。
一開始,少年父親的阿爸離開土地,還沒習得在都市做一枚小螺絲釘的技能,日子不免茫然。不過,他有一雙勤奮的腳,很快地成為沉默奔行的三輪車伕。然而,生活重擔沒有卸下,反而變得更具象,日夜拖磨著他疲憊的身軀。直到跑車途中撞斷了腿,才被迫躺下來,獲得長久以來真正的歇息。可是,歇息對艱苦人而言總是奢侈品,睡夢中,他踩踏板的腳反而轉得更快,直直踩往那個讓一家人不再飢餓,卻始終也到不了的遠方。
雲嘉南的男人與女人們,用他們曬得乾糙粗黑的肉身,做為60年代讓台灣城市飛速前進的柴火,卻也經常就這樣燃燒殆盡,被時代輾過,灑落成點點星灰。
因為阿爸那一條被碾斷的腿,少年父親第一次走入台北城。做為長子,清早就被不識字的母親送上火車,除了安慰在異鄉負傷的阿爸以外,也要帶著讓阿母安心的口信回來。
嘉義火車站曾經是連結山海通路的重要轉運站,也是戀人們許下山盟海誓,卻都將成謊言的隘口。除了被列車拋下,逐漸縮為一顆逗點大小的阿母身影以外,火車站天橋上還懸掛著許多天下父母心,望著一批又一批青年男女遠行到都市,創造不屬於農村的經濟奇蹟。不過,少年父親有一種鄉下男孩不解人事的傻氣,沒察覺到天橋上母親擔憂的表情,一上火車就戇著混沌的頭殼,貼著車窗,讓海岸從視線退開,好像退到了盡頭,夢想中的台北城就會緩緩浮起。
一個真正的都市會生成什麼款呢?鄉下孩子幾乎坐不住,興奮地想像著。
很快地,少年父親發現自己頭殼鹹鹹,漲滿了海水,藍天白雲之下,蚵田、魚塭靜靜展開,卻搜尋不到任何一個素材可以去構造都市景觀。當然,對從未離開過海口小村的孩子而言,都市畢竟是比海平面更遙遠的概念吧。
九個小時的車程裡,少年父親用阿母送行時塞進他褲襠裡的十二塊買了火車便當,一咬進去,濃濃的豬油香、脆感青江菜、滷得黑亮的蛋就在嘴內底核爆。那是少年父親此生最快樂的一天,旅途中,他不曾憂慮摔斷腿的阿爸會不會再也踩不動三輪車?整個家是否會支撐不了而崩解?火車便當帶給他味覺上從未體驗過的豐足,讓少年父親從腹內升起一種簡單而美好的情感,徹底忘卻此行任務該是多麼焦心,兩顆招牌蚵仔門牙情不自禁蹦躂出來,傻咧咧笑著。
於是,火車還沒入站之前,少年父親就得出了一個結論:台北一定就像一盒有豬油飯、青江菜、滷蛋的火車便當。
即便在後來的歲月裡,他變得世故,見過現代化城市裡所有疏離、歧視與欺詐;在台北娶妻買房生子,取得社會地位,真真正正成為了一個富足、成功的都市人,並且絕少感到匱乏。然而,最初那段旅程中,火車便當之於台北的隱喻,對中年父親而言,仍然是一句無法回返的鄉愁。
有些時候,離開一個地方,那個地方才會在概念上成為真正的鄉。
於是,初中二年級,少年父親跟著阿母北上以後,嘉義東石就真的變成這一生中再也無可回返的鄉。
時間讓空間有不可逆性。反之亦然。
50年代的「搬家」,還具有一種古典意義,每一次離開都是永別。然而,對貧苦之人而言,離別的重量和要帶的行李一樣輕,除了生存下去,沒有什麼特別珍貴,也就沒有什麼不能丟棄。少年父親搬離嘉義時所有的行囊,除了幾件滿是補釘的衣服之外,還有一頂學校發的塑膠圓盤童軍帽。他悉心擦好,慎重其事地挽在手臂上,護身符一樣,彷彿那是唯一配得上都市新生活的行頭。
然而,生活是一列永遠趕不上的火車,殘酷地飛馳而過,任你在後頭追趕吠叫也只是徒勞。少年父親一家七口在台北團聚後,落居在三重淡水河畔的貧民窟裡。都市討海人絕大多數逐水而居,那並非對故鄉空間的緬懷,僅僅是因為河畔易氾水災之地乃最低賤、難以發展的區域。於是,海口阿爸們又口耳相傳、摸石頭過河,一個拉一個往河畔求生去,逐漸在三重、板橋、新莊、永和橋下搭起破敗的木造聚落。即使生活裡還是有許多如狗吠火車般徒勞的嘗試,這些河口新移民也會互相勸慰:「狗仔睏治通路櫃,有福不知惜。」一隻有櫃子可遮風避雨,有火車可追的狗,還有什麼好怨歎的呢?
因此,移居台北的頭幾年,少年父親的都市印象還不如當年那一盒火車便當鮮明,也從未產生如新感覺派筆下人物對現代性「Light, Heat, Power!」的驚異。貧民窟的歲月,一家人擠在四坪木造房內,光線昏聵,冬季寒,從淡水河上一路捲過來的風尤其悽冷,這樣的日子沒有Power,沒有驚歎號,只有虛軟、看不見盡頭的刪節號。整個河岸貧民窟都由中、南部家庭組成,黏膩的海口腔在風中不曾潰散,放眼望去都是給太陽烤得焦黑的皮膚,讓少年父親經常有一種其實從未離開故鄉的錯覺。
然而,這種只是換個村落生活的幻想,一直到他開始上學之後便裂解了。
從淡水河岸出發,少年父親在夕陽中得踩上一個小時的腳踏車,越過長長的台北橋,往右拐進承德路,才能趕在夜間部開課前奔進教室裡。成淵中學是都市感逐漸具體的起點,從少年父親蚵仔門牙邊擦出的鹽漬國語,同樣沉甸甸,揪緊尾音一路向下,與同學們習於說國語的嘴巴都不一樣。這股「我怎麼不一樣」的感受,原先只是懵懵懂懂的輪廓,終於在升初三的暑假爆發成一記無可忽視的警醒。
這一記警醒還伴隨著對階級差異的初體驗。
不拉三輪車的少年父親阿爸,向同鄉習得了烤わがし(和菓子)的技術,揉進更多麵粉,將精巧的日本點心改造成台灣勞動階層喜歡的飽實感。有很長一段時間,少年父親阿爸就這樣賣力地在廚房扮演「哇嘎西」阿爸,生出一顆又一顆胖呼呼的和菓子,躺在熾熱的烤盤裡,替這一家人在城市裡爭取生存機會。少年父親白天也跟著阿母到工地當挖土工,暑假則到牛皮工廠熬牛皮膠囊,憨憨的腦殼頂在黑黑瘦瘦的身軀上,隱沒在一群工人中,就像一顆彆扭的大頭釘。也就是在那條生產線上,他一抬眼就撞見隨著廠長老爸來巡廠房的同學,對方立刻端出小老闆的態勢問:「怎麼?原來白天你就在這裡工作啊?」此刻,那一口燙得平整的國語,不慌不忙輾過他的胸坎,少年父親掩住蚵仔門牙,垂下眼,怎麼樣也不願開口回答。
從今往後,少年父親就決心換一付新嘴巴。
不上工的時候,他捧著字典,按著注音符號大聲朗誦,一字一字沖洗他的國語。每洗過一次,藍天白雲青灰海浪之間,一喇又一喇的蚵田風景就退得更遠,一直到再也沒有人能在他開口之後,指認出那片鹽漬過的鄉。
操著一口好國語,成為一個文明的都市人後,走出河岸泥灘地的中年父親在普世意義上,可說是完全地成功了。此後,他絕少再夢見那個戇著頭殼的漁村小男孩,趴在火車車窗上,腿上枕著一盒火車便當,想像著無可想像的台北。●
【評審意見】
移動的根由
◎陳列
文字活潑獨特,時而嘲謔卻又含帶著心酸,時而銳利卻嚴肅而細緻。有許多光彩煥發的句子,更有許多深刻的洞見。這不僅因為作者對文字修辭藝術的理解和掌握,更來自於敘述者敏銳的觀察、感受和詮釋的能力。當然也來自於對少年父親生命經歷的深情懷想和體恤。全文不僅生動記述了少年父親,和父親的個人或整個家庭掙脫窮困局限的求活意志和過程,也呈現了台灣在一大段年代裡,人們的生存境況,城鄉甚或階級的差異,以及社會力移動的若干苦楚根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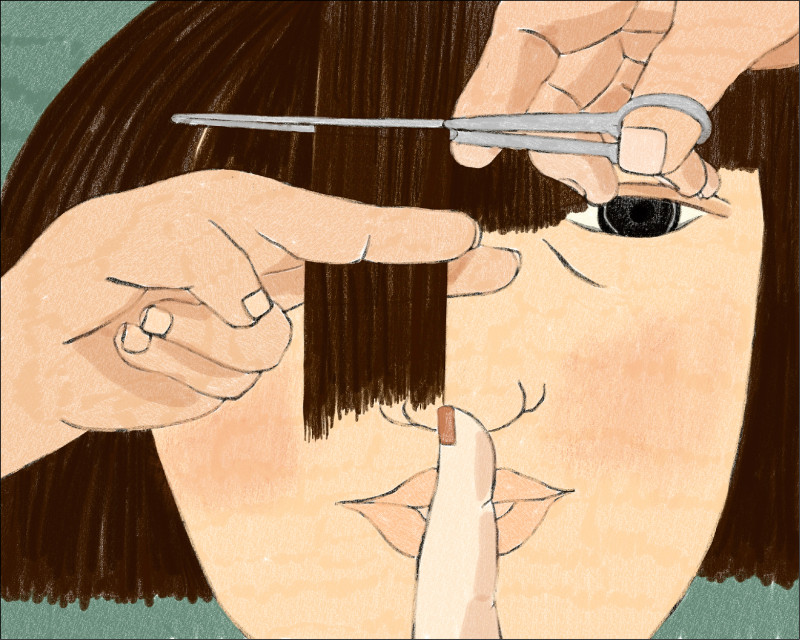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