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閱讀小說.長篇精摘】 - 3之3 永別書:在我不在的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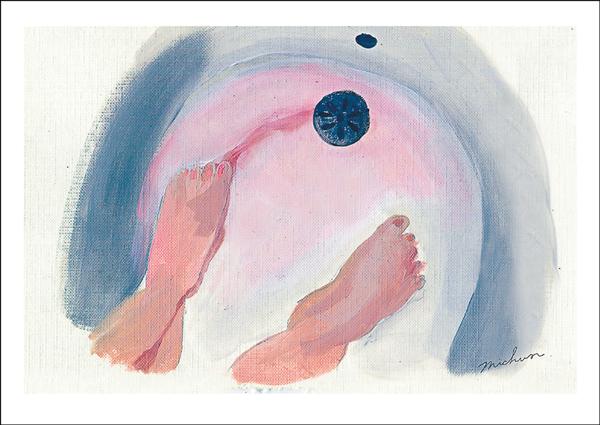 圖◎michun
圖◎michun
◎張亦絢 圖◎michun
幾年前母親節前後,客串一日孝女那樣,我買了票,請我媽去看在兩廳院上演的音樂劇《渭水春風》。那是我從歐洲回到台灣來後,看的第一場表演:如果反國光石化時,「拷秋勤」那些樂團不算的話。我原來也很擔心:殷正洋能唱蔣渭水嗎?我不覺得蔣渭水那角色,光用美聲可以撐起──結果令我非常驚訝。我以前沒有喜歡過殷正洋。在音樂屬性上,我一直學古典的東西,但我更喜歡噪音或重金屬:他們力求失真的嗓音,我認為那才是音樂中的音樂。我媽也喜歡嗎?喔我但願不至於。我當然沒有介紹過她聽,不然她恐怕是會想插上一腳的。我知道,這幾年她自己會不遠千里跑去聽「春浪」,但說真的,我寧願不繼續想像下去。
《渭水春風》演出時,我哭了好幾次。自己都覺得很不好意思。我不得不在中場休息時跟我媽解釋:我只是想到我青少女時,那時絕對想像不到可以有這一天──看到台灣史的東西在國家劇院上演。國家劇院那時就有了啊,三月學運五月學運,國家劇院是個布景嘛。差別嘛,就是那時候沒有摩斯漢堡吧。高二時有個同學帶一本宋澤萊的書到學校裡,你知道書名叫什麼嗎?叫做《大聲喊出愛台灣》(註3),我們緊張地傳來傳去,像是那是個未爆彈。那就是個禁忌。書也許不禁了,但心理上我們覺得它與違禁品不遠:就算不是海洛英也是大麻,你懂嗎?不可以的。那個書名。今天你讓一個七年級看,保證他覺得莫名其妙,愛台灣都可以寫在餅乾的包裝上了,「大聲喊出」是什麼意思?是發生了什麼事,要大聲喊出那麼普通的事?
後來我媽和我去附近的一家豆漿店吃消夜。我就說啦,那些保存語言與記憶的重要性什麼的,你知道歐洲他們經過集中營的慘劇,多的是這一類的討論。我有那種愛好歷史的癖性,不是懷舊,更像一種,對科學精神的追求。我說著說著,我媽說了一句話,我就閉了嘴。她說:「妳真是像極了妳阿公──阿公還在世時也常說,不能讓國民黨毀了我們的語言與文化。」不不,我阿公不是什麼名人,不是。──剛剛說到國家劇院不是嗎?
有次我從凱達格蘭大道離開,大概是反核之類吧,我因為去找便利超商上洗手間,所以多走了一些路。走到國家劇院不遠處,和一群也是從方才集會遊行散開了的人同在一起,等一個紅綠燈。幾個女生,不認識的,但其中有個是呂赫若的後代,正在說一個笑話:有天她碰到個人,那人告訴她說,他是某某某的後代。這個人名我不太確定,因為當時有車聲與風聲,聽著像是鍾浩東。但也許不是。然後這個呂赫若的後代就說啦:那正好啦,你外公是某某某,我外公是呂赫若。其中一個女生就問啦,那你們有沒有相擁而泣抱頭痛哭。這時這個呂赫若的後代就說了:「才沒有呢。我們同時說了:幹你娘咧。」這群女生就一起笑得東倒西歪──不過這不是我要說的重點,這之後,這個呂赫若的後代又說了,非常語重心長地:「呂赫若是個真正的才子。」
沒有人接她的話。我想是因為她們雖然知道呂赫若是個名人,但她們沒讀過,甚至不太有聽過。我當時很想開口道:這是真的。Je peux vous confirmer.(我可以向您證實)──當時我剛回台灣,情急時頭腦就會出現法文。但我終究沒這麼做。我等著等著,但都沒有人說話。
我心裡很難過──你可以想像卡繆或雨果或沙特,嗯沙特應該沒後代,總之那就雨果的後代好了,要對同儕說:雨果是個真正的文豪。就連對我這樣的外國人,一個法國人都不必這麼說。當然不是說介紹呂赫若介紹得彷彿他是個地下樂團的主唱那樣,就會怎麼樣。不過這還真是慘啊。而且現場既沒有人說:「那還用說。」也沒有人接口:「我有讀過耶。」──彷彿呂赫若還真是個地下又地下,來自愛沙尼亞的鞭笞重金屬樂團主唱。而且成軍不過一個月。臉書上只有十個朋友。
要是她可以不用說「呂赫若是個真正的才子」──該有多好!
我是說,要是記憶這事,可以完全擺脫掉家族血緣而存在就好了──她覺得有責任告訴大家,呂赫若是個才子,因為她直覺,家庭之外的人的記憶不可靠,人們不會有效地、持續地,記得此事。她的同伴們的無言,證明她的判斷沒錯,在我們生活的這個歷史時間點上,人們還不怎麼記得呂赫若。所以,她仍然是無法消滅她的記憶的人。這件事,真的,並不美。
我認為美麗的事是,說到呂赫若時,她可以說:「說真的,雖然他是我外公,我卻不知道他是誰。」
「我有讀過他的東西。」一人道。
「我聽我姊姊說過,呂赫若他很了不起。雖然我沒讀過啦。」一人道。
「妳竟然不知道妳外公是誰?連我都知道。」另一人道。
如果我們的記憶,可以在別人手中生長,那該多好。如果我們的記憶,留在我們手中,那都是不得已的,那是一種情非得已。沒有人願意去的勞動服務,沒有人要出來選的班代表。有些個人記憶它像這樣。別無選擇。記憶的別無選擇,是人生的最高刑罰。我付出過代價,我懂,並且我要停止它。
我外公不是呂赫若之流,他是個普通小學教師。但不管他是誰,我一點都不願意像他──因為像他就是像我媽,像我媽就是個大災難。或是音樂或是台灣史,這兩者總會有一個東西讓我和我媽看似和解──而那個和解東西,無論表象或實質,都是我嚴厲拒絕的。我放棄過音樂,我或多或少也放棄過台灣史,但我要走得更遠更遠,你會看到,我消滅我的記憶。
我消滅我的記憶。妳說過,妳先是消滅它們的強度,但再來呢?我是後來才知道,消滅強度,我就幾乎成功了百分之九十九。但問題是,就算是躺在玻璃棺材裡的白雪公主,也會有什麼東西讓她睜開眼──那是什麼東西?王子的吻?我想起來了,這個故事要是隨便聽聽也就算了,但如果你認真地慢速播放那個經過,你不覺得挺可怕的嗎?不管是白雪公主雖死非死,或是只因為被以為死去,那什麼王子就去親吻她──好,反正童話就是那麼回事。不把恐怖當恐怖。但就像都躺進棺材的白雪公主會睜開眼,我以為已經沒什麼生命跡象的記憶,有時也會忽然冒出來,像壞了千年,不經修理就自己好了的咕咕鐘:嚇死人地開始報時。小朱,第一個我曾經想忘卻忘不掉的記憶,就讓我不只一次經歷了這事。
我離開台灣的那十年,本來是個很好的契機,讓我完全忘記小朱。我自己很清楚。所以當我抵達另一洲時,我身上沒有任何東西,是讓我們可以互相聯絡的。沒有照片、沒有地址、沒有電話號碼──那時電郵信箱已經開始使用了,但還沒有全面流行起來。想到這,我是非常快樂的。我覺得在我二十七歲時才坐上的這個飛機,是我十三、四歲就想坐的。我坐上的雖然是普普通通的民航機,心情卻像是坐著一部好萊塢電影無緣無故就要出現的噴射機,〈乘噴射機離去〉,是的,啊是的。在我心中有著噴射機,愈遺忘,愈快樂。
我幸福地過了幾個月。幾個月。有天我走進當地一間放藝術片的電影院裡,坐著等電影開演,突然,電影院裡開始放惠妮.休斯頓的那首歌。波赫士有個故事不是說了嗎?有個人聽說他某年某月某日會碰到死神,因此拚命逃跑,一直跑到個沙漠;結果他和死神就在沙漠裡相遇了。死神還笑他:你原來要是不跑的話,還不會遇到我。我是很理智的人,我既沒有想到命運,也沒有責怪那家該死的電影院──只能說音樂這東西,就像香氣或性欲一樣,除非你能完全隔絕,一旦它滲入,它就是滲入了。我也沒有像尤里西斯遇到塞蘭女妖那樣,知道要塞住耳朵:我對自己太有信心了。
當時還不怎麼樣。夜裡我在浴室裡,洗澡洗到一半,就出事了。血水先是從鼻子裡像關不住的水龍頭那樣地流個不停,接著一個浴室地板上都是血水,卻不是從我鼻子裡流出來的。我的經期上個星期才結束,「好朋友」一向像瑞士錶一樣準確。這只能說是一次異常大出血。要不我是快死了,要不就是受到太大刺激。或是以上皆是。以一個外國學生的身分登陸歐洲,我當時幸福得忘記我是一隻筆,但是誰說筆是寫作最重要的工具?血是更無限的,那像靈感一樣的滔滔控訴──潮水原來並不依時而來,噴墨──它根據的是更隱密的法則。
惠妮.休斯頓去世那週,我把那支歌放出來給自己聽,想要知道,我會有什麼感覺。但是令我自己都難以置信地,我發現,我竟然已經失去了感覺。就像失去視力或是聽力一般,記憶也會走到,記不住的那一天。原來凡事真的都有盡頭:遺忘已悄然開始,就在我不注意的時候。放任遺忘自然發生,這當然也是可行之道。但我想加速它的進行,在死亡來臨之前,搶先一步,成為一個:一無記憶之人。我將記錄這個過程,因為我相信,在芸芸眾生之中,我一定不是唯一一人,曾在人生的某處停下,對自己說:要是我能遺忘一切,這將多麼美好!
研究說,金字塔蓋起來的祕訣,都已失傳。還好是,我從來都不想蓋金字塔。但是我想知道怎樣可以使它倒塌。塵歸塵,土歸土,記憶者,都消滅,我願留下之物,惟有倒塌學。●
註3:此處小說敘述者記憶有誤,正確書名是《大聲講出愛台灣》,正確的作者是林雙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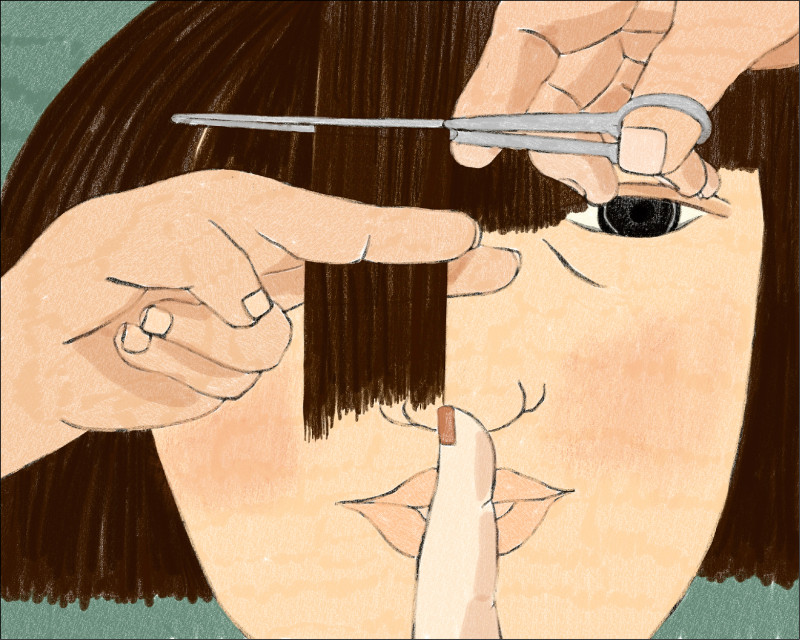




網友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