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自由副刊】【第九屆林榮三文學獎.短篇小說獎二獎】 兩棲作戰太空鼠 〈3之1〉
 圖◎吳孟芸
圖◎吳孟芸
作者簡介:
 ◎李奕樵
◎李奕樵
李奕樵,1987年生,長於南郡。2001年體制外全人實驗中學肄業。曾獲耕莘青年寫作會傑出會員。現為軟體工程師,亦為書評電子刊物《祕密讀者》網站的開發與管理者。
得獎感言:
感謝翊峰、黃蟲、小風、宥勳、書羽、何瑄、雲顥、進韋、逸勳、致中、白哲、佳芸、慧潔、琬融,這些半年來被我以文本騷擾還願意回報想法的人。
感謝榮哲、儀婷,守護著我深愛的耕莘青年寫作會與「搶救文壇新秀再作戰」文藝營。感謝芸如,為了至今我所得到的。
★★★
◎李奕樵 圖◎吳孟芸
沒有威嚇。我只是輕說了聲:跑。
他立刻從地上彈起身子,在小小的牢室裡,跑了起來。沿著四方牆壁,繞著圈跑,跑得很快。圈子很小,他得向中心斜著身子,以畸形的身姿跑著,好抵抗離心力。不停旋轉,像一只無奈的鉛錘。
在這之前,我無法想像一個人看起來不像一個人,而像鉛錘。所以我在心中默默推算他的身體重心位置、體重、奔跑速度與身體內傾角度的公式。這樣我就能從他傾斜的角度,大概推算出他將跑多久。
早晚各一次,跑到規定的圈數為止。這得花上一些時間,但我不必費心思,他自己會報數。在我之前的人會大聲喝令,要他盡可能地跑大圈一些,擴大成更傷腳的,緊貼牆壁的四角形路線。不過我不喜歡大聲說話,我只想聽。我只聽他跑步的踏地聲,並且讓他知道我有在聽。
我不免認真思考:為什麼籠中鼠會在輪上奔跑?
還有,為什麼我可以忍受呢?做為一個觀看的人。
鼠群在我皮膚底下蠢動,沿著大腿內側一路開隧,大規模鑽爬上腦。牠們用尖軟的鼻子戳戳我的大腦皮質,推拉神經元像操縱桿,擔任駕駛員的少年鼠表示系統狀況良好,正向能量循環中。
這是座彈丸之島,幾乎沒有平地,倒是有無盡的隧道。我們睡在隧道裡,隧道裡有很多房間。我分配到的寢室有兩管日光燈,流明極低,很難在裡頭閱讀。躺在床上,我聽不見通風口風扇運轉的聲音,也許根本就不存在風扇。海島的夏天是四十度的嚴酷濕熱。因為通風不良加上做為恆溫動物的原罪,夜間寢室內濕熱更甚,綠色的床墊永遠是濕的,難以排汗散熱。天花板兩盞風扇轉動,在濕熱中攪動熱風。
有人在睡夢中中暑。
我們得拚死喝水,強迫自己排汗。但部隊裡沒有海水濾淨機,只有島上小小水庫積留的微溫淡黃土水,還是每天限量的。他們說,不過在二十年前,這座小島上塞滿三萬官兵,現在的資源可用充沛稱之,惜福啊死菜兵。
一開始我還在心裡試著計算那些不知名雜質的含量,每一個夏夜都在喝與不喝之間,悲壯決斷。後來我掌握了在不驚擾細小沉澱物前提下,平順飲水的技巧。再後來,我就說服自己,消磨雖然能累積成死亡,但畢竟可以忍受。
小島上很容易就能聽到「正向能量循環」這個詞。公布欄上,蔣公說,禮貌是宇宙的真理萬物的道統。宇宙有真理,還是白色的。
我本以為禁閉室是在充滿白色光源的隧道裡,但不是,它被設置在山地公路旁,廢棄已久,藤蔓穿繞每一個鐵窗門柵。看上去與島上諸多廢棄營區毫無分別。為了這個個案,特別重新啟用。連上通信專長的中士帶人牽線,一上午敲敲打打,裝上監視器。中士很緊張,很擔心在未來幾天這個監視器與這條線會因為任何原因故障,任.何.原.因。
我想問他,為什麼非得將自己裝成一個瘋子,非得試圖毆打軍官,非得試圖用這麼笨拙的方法逃離。
但只要一看到他的臉,我就沒辦法問。那是一張絕對順從的臉,因為恐懼。而我是恐怖風景的一小部分,無論說什麼都是一樣的。
但我知道他獨自沉思的時候,在想什麼。
一定是宇宙。因為哪裡都去不了,所以我們必然思考宇宙。
如果過得很辛苦,也會思考禮節。
島上老鼠特別多。士兵在營區各個角落安置大量的捕鼠籠,甚至是自己用寶特瓶跟木板製作的簡易陷阱:將兩公升寶特瓶切掉三分之一,在邊緣安置一小片木板,木板內側放一小塊食物,外側則架在洗衣桶上,放在床底下過幾天也能抓到老鼠。老鼠會沿著軍靴爬上洗衣桶,然後再連著食物跟木板掉進寶特瓶裡。寶特瓶底部用一顆螺帽鎖緊在一片厚三合板上,經得起老鼠的掙扎。
那些老鼠都會是玩具。牠們的死法端看當時流行風格而定,只要不弄髒衣服或環境,任何方法都是可以接受的。有一陣子大家喜歡將老鼠拋到半空中,然後試著用金屬球棒打出去。
球棒揮空,老鼠掉到地上也沒關係,老鼠的四肢筋骨通常已經剪斷,這是大部分遊戲前的標準程序。四肢剪斷後的老鼠在地上就能看出個性。軟弱的會因為劇痛放棄掙扎。另一些能忍耐痛楚的能慌亂空轉,掙扎得極快但移動得極慢。就有人以戲謔的聲音說:唷,是條硬漢呢!
在半空中被球棒擊中的老鼠多半只會噴出一點血沫,然後飛出幾公尺。打中的人會大喊:Home Run!然後原地小跑一圈。
但有打者揮棒太用力,直接把老鼠打成血肉煙火,四散飛濺的內臟沾到彼時還正在狂笑的義務役下士班長。班長很生氣。出於對同袍的禮節與義氣,這個玩法從此就被眾人自動封印。
新的玩法改成用兩根金色針尾的大頭針插進大老鼠的雙眼,直壓到底,稱呼牠為「金眼鼠王」,這個名字不知為何可以逗很多人大笑。雙目皆盲的金眼鼠王,帶著沒有瞳孔的兩顆金色義眼,在寢室裡亂竄,一尊神像亡命天涯。
我看著這一切,在笑聲中毛骨悚然。為了「正向能量循環」,我每每強迫自己跟著大笑。久了,也無法分辨是否該恐懼這些笑聲。
老鼠死的那瞬間多半已不會叫。只有在恐懼的前戲中,老鼠才有機會尖叫。但鼠的尖叫確實地刺入我的腦子,那是形而上的精子,總能在夜夢中熟成一隻完整而潑野的肥碩巨鼠。
隨時間過去,牠們軍容愈發壯盛,那些死前經過改造的老鼠,像是金眼鼠王、藍天翱翔棒球鼠、七俠五義戰隊鼠、無腳土龍鼠、水鴛鴦神風鼠(有分口銜組跟後裝推進組)、二足直立進化鼠、二維平面鼠、線控人偶鼠……牠們一字列開,已經夠組一個特戰排了。
綠衣黑褲白布鞋,早晚各跑三千,我們從小沙灘沿著海岸線跑到港口,再跑回來,來回三趟。我跑在鹹鹹的海風裡,試著回想夢裡是不是有人曾對我說了什麼。
陽光穿進我的瞳孔,再穿進小小觀測鼠的瞳孔。觀測鼠報告,標高一米六,系統狀況良好,均速行進中。
回到寢室,我脫鞋,從布鞋裡掉出半截鼠頭。
我跟鄰床的學長說,我被盯上了。
「誰教你都不跟人說話,這樣被誤會剛好而已啦。」學長說。
「那怎麼辦?」我問。
「幹。」學長笑了:「啊不就開始跟人說話,讀書讀到憨喔?」
學長說,這裡只有沒權限光明正大搞你的兵才會這樣做,這種小意思啦,了不起頂多就是退伍前在你屁眼塞整隻老鼠而已,死不了人的。
真的有人被這樣對待?
「我也是聽人說的啦。」學長呵呵笑:「大概四、五年前,迫炮連還沒被縮編的時候,有個快退伍的白目兵,半夜被一群人叫起來打,聽說有被拿老鼠塞屁眼。幹如果真塞得進去就神了。」
幾個學長聽到也開始加入話題。說那是終極必殺技,要滿足多重條件才可以發動,像是需要事先擴張(可以用守衛棍)啦,還有大量凡士林(安全士官桌放的護手霜不知道夠不夠潤滑)之類的。
「戰術執行就是要物資、人力、技術三者同時到位,缺一不可。我們連在這方面的訓練都可以推廣到日常層面,真是太精實了。」有人說:「指揮部應該要找時間獎勵我們。」
「這就是自強不息啊。」有人說:「我們求的也不是榮譽,只是滿足學習欲而已。」
沒有人談論我鞋裡的鼠頭。沒有人在看我。
我站在談話者的圈外,手拿半顆絕對塞得進自己屁眼的鼠頭。
夜裡,半顆鼠頭入列。代號小可愛。小可愛不占空間,靠牆列隊時甚至可以直接把半顆腦袋接在我的腦殼上。跟我一樣沒啥存在感,也不太說話,因為沒有肺。
午夜站哨時,小可愛會跟我一起用半顆腦袋思考宇宙。本質先於意義而存在。生命是什麼呢?暴力是什麼呢?掙扎又是什麼呢?
島上星圖繁麗,我以為視力差就看不到星星,我錯了。我甚至能辨認出橫貫天空的銀河。即便是沒有月亮的夜晚,我都還能藉著星光視物。它們是如此明亮的存在,我懷疑除了穴居生物以外,地球上的生物可以理解在黑暗是怎麼一回事。
只有像人或鼠這種穴居動物,才有資格思考真正的黑暗,以及黑暗中生存的技巧。
在小可愛報到之前,這樣的共處時間是很罕有的,因為下半身還完好的嚙齒類太喜歡打炮了。我有一點點羨慕牠們,也覺得很寂寞。做為一個巨大的人類士兵,安靜佇立,荷槍實彈凝視世界,我很寂寞。身邊士兵群體起立,唱軍歌,腦袋空空如也報數時,我覺得很寂寞。腦內眾鼠歡騰,銜咬各式記憶想法欲望穿進穿出時,我也覺得寂寞。
所以當我獨自面對深夜的星空與海時,我很高興有小可愛的存在。我都快要感激那個不知名的,將小可愛放進我純白運動鞋內的同袍了。我跟著小可愛一起思索我的寂寞與陪伴的本質,思索所謂的高雅與正義或許並不存在,只是欲望被培育或裁切成各種不同的樣子而已。
集合場上,總是會有幾隻狗蹓躂過來。大概凌晨3點左右,遠處有犬吠傳來。這邊的狗表示不能忍,紛紛跑到高地最佳開火位置,跟著吠回去。
眾鼠鳴鈴,緊急召開會議。
那個跑位實在精妙,必須跑過半個營區,爬上山林間黑暗的階梯才能趕走那些狗。而查哨官隨時都有可能會出現,如果在去趕狗的幾分鐘內(牠們還有可能根本不理人),查哨官就翩然降臨,那人類士兵的我可能會被連隊主官幹到飛起來。
我呆站了幾分鐘,等著鼠們舉爪表決。缺乏決策效率是逃避獨裁者的機會成本。
「幹,你都不管狗的喔?」有人在我背後說。
我回頭,是安全士官。因為連上士官不足,是一兵代站的。照規定我不必喊學長好,我就不喊了。
「牠們在很遠的地方叫,我走不到。」
「幹。」安全士官說:「還真有藉口。」
「我現在就去看看。」我說。
「去!讓這些死狗吵到連長睡覺,我們就都完了。」
我繞過集合場,跑到樹林裡的階梯。狗叫聲還是有段距離,但很響亮。
我不敢大喊,用手電筒照了照四處,希望可以給牠們施加一些壓力。
有幾隻狗大概有被我的手電筒掃過,稍微安靜了幾秒,又跑到更遠的地方去繼續互吠。
我回到崗位。
報告,牠們都在樹林裡。我說。
「媽的,裝無辜咧。」安全士官翻白眼:「等那些蠢狗回到這邊時,跟我說一聲。」
報告是。我說。
狗群回來時。我按了一下對講機,通知安全士官。
安全士官帶了一個包子出來。
「這本來是你今天的夜點,當做學費,教你怎麼管狗。」
他喂一聲,舉著包子,把狗群吸引過來。(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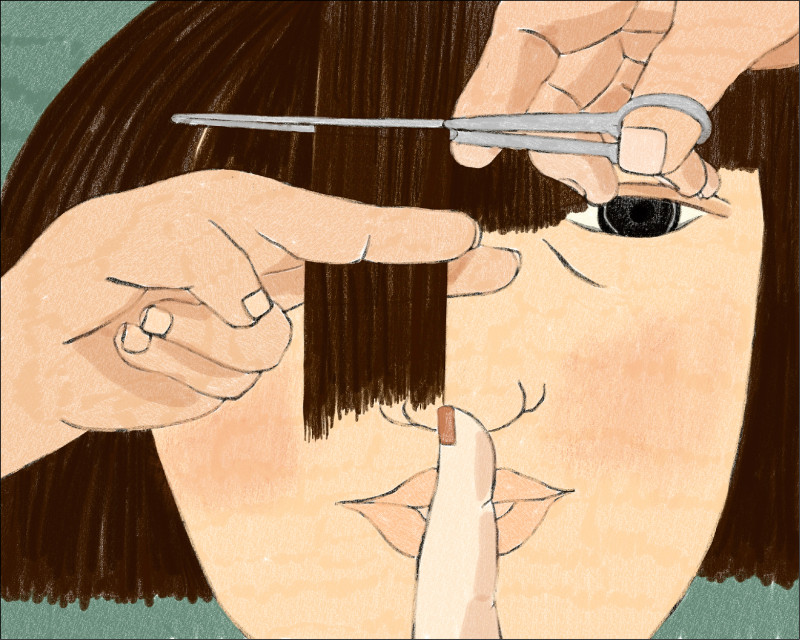




網友回應